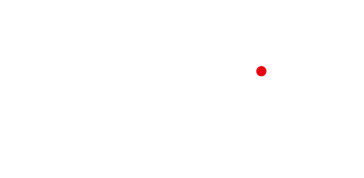Q1、我們一直很好奇,品文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研究女性主義這個議題的?
A:其實我認為我開始研究女性主義這個議題是非常非常晚的,因為我其實一直很沒有女性意識,因為我從小其實不是有那麼典型的女性特質,我在大學的時候其實有修過第二性的通識,但是我覺得唸完之後我也不是真正非常的積極投入性別研究,我只能說我意識到性別的存在,但我並沒有很積極的去研究,我剛到台北念書的時候,參加了第三屆的「下一個編舞計畫」,然後那一年的策展主題是「純」pure,純,我做了一個獨舞叫做「異鄉」,其實可能表演藝術評論台是找得到這支舞當初的評論,對我來說最深刻的是在演後座談會有一位觀眾他舉手問我說:「你是女性主義者嗎?」那個當下其實我有一點嚇到,因為這位觀眾看起來真的很像是經過隨便買票進來的那種,隨機的觀眾,他不太像是我以前熟悉會遇見的舞蹈觀眾群,我也不認識他,他看起來好像素昧平生,從來沒見過,我非常多年沒有聽到女性主義這個字了,甚至我可以說我在北藝大待了四年,我也不記得有誰去向我提出女性主義,所以我馬上就意識到「哇這個問題其實是非常的銳利的。」但並不是讓我不舒服的這種,然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就花了半秒鐘我就說:「對我是。」(笑)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一個好的提醒,我一直認為他是我的貴人,如果沒有他我可能今天還不會投入性別研究,甚至是女性主義的研究。然後…我也沒有馬上開始女性主義的研究,但我好像就有一個認知,就是知道說:「喔!我就是會被認為我是一個女性主義者,而且某種程度上我也同意,我是一個女性主義者。」
我真正的研究應該是從2016年年尾的時候,在台北雙年展跟Xavier Le Roy retrospective 畫作回顧的舞者的時候開始,我逐漸成型了我的女性主義研究,或者是說我的性別研究,其實跟Xavier也是一個奇緣,因為在排練retrospective這個作品的時候,其實也是一個非常別緻的狀態,我想表演藝術評論台應該也找得到這個作品的評論,但Xavier他問了我一個問題,他問我說:「你有想過要變性嗎?」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問這個問題,但當然這個問題在他問之前我已經問我自己很多次了,這個答案就是:「我想變性。」然後我的確也做了非常多的在台灣要怎麼變性的搜尋,是非常複雜的過程,所以在變性的這一塊台灣並不是太友善,
然後那個時候開始在北美館做了一很正經的工作,每天必須要去上下班,我的第一個性別研究就從這個每天固定打卡上下班的痛苦工作表裡面就開始了,我從一個對話裡面是跟我的好友,sophia,我就說:「我想要我的英文更進步,我想見一些有趣的人。」他就說:「那你要不要用用看tider?」他就給我看了他tinder的profile,他就說:「你看我都放一些很奇怪的照片。」於是我就透過呈現一個怎樣的蘇品文會吸引到類似的人,或對這個蘇品文感到好奇的特定的人,然後我的性別研究就從「tinder date」開始,實際上我有感覺到在台灣的整個風氣裡面,當我把tinder date變成一個研究,並且時不時定期的po在facebook上面的時候,就有帶來一些所謂的觀感不佳(笑),我認為這就是普遍的性別研究者會遇到的問題,然後這個tinder date的研究逐漸地變成人性肢體語言研究,就是好像你假定呢這個社會是由兩個性別,生理男,生理女然後你又先假定了他們都是異性戀,就當一個男的遇到一個女的之後他們就可能戀愛,他們可能性交,他們可能發展出一段透過基本性別而延發的關係,所以大概可以聽得出來,我的研究方向基本上跟性學還有行為學比較有關係。
因為我不是科班出身的編舞者,我比較傾向哲學,然後當我在尋找動作素材以及我又意圖希望著個動作素材可以跟我的觀眾有連結性的時候,我就回想:「台灣人的身體語言到底是什麼?」因為我每天去搭捷運我看每個人的身體語言就是拿著手機在滑而已啊,但我的編舞當然不能從這裡去啊,所以我就想:「哇到底有什麼動作是我們的共同經驗?」是更靈活,所以它就回到人的基本需要,吃飯、滑手機、做愛。所以就是作為一個編舞者為什麼我選擇性學跟行為學去做我的身體研究,我認為它的原因是在這,因為那是一個幫你製造動作並且形成動作的意圖,你真正的動作的流動的,很自然或者每個人都務必會去面對的一個個人問題。
Q2:什麼樣的契機是讓你希望在今年度做這個女性主義工作坊?
A: 我想先回應一點,其實在台灣的藝術工作者都相當的多元,他可以當舞者,他也可以做編舞者,同時他可以教課,更遑論他教課的對象可以從小學到中年,甚至到老年,然後各式各樣不同的舞蹈類型,這是台灣的藝術創作者非常多元的彈性,我也是在這樣的歷程上上來的,但是逐漸的我發現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慢慢有一些工作開始不適合我了,像是我嚮往的性別的多元實現,回到個人的性別的多元呈現,而不單純是你的性別跟我的性別不同,而是我本人也可以有一些不同的選項……..嗎?
然後我就發現作為一個積極的女性主義者,的確有些工作非常的不適合我了,並且會開始對我的觀眾營造出某一種叫做「我不認識品文 ,品文的那個研究跟她在舞台上的呈現,讓我對品文這個人到底是誰感到很模糊。」所以我的專業層次跟我的研究方向開始分道揚鑣的時候,我就知道我好像必須要為我的整體的生活或將來的規劃有個更明確的決定,也就是我好像必須要捨棄一些我認為沒有支持我研究方向的工作。做了一些取捨,那也就是為什麼去年會有《少女須知》這個作品,因為我就理解到我必須要確認和行動,去為女性主義這件事情工作,特別是如果我也理解到身為一個生理女以及女性主義者,並不是我說:「好現在這個排練有三個小時的時間,我跟我的性別一點關係都沒有!」(笑)好像沒有辦法這個樣子去割捨,所以我就理解到如果我已經相信女性主義是我想要去工作的,我就應該要真正選擇一個路線。對所以去年就有了少女須知。
為什麼會想辦女性工作坊,因為我沒辦法說:「現在十分鐘下課時間,我不是一個女人,我的性別現在與我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可以切割開來。」實際上是辦不到的,就是關於性別還有身體,身體與我,這個東西是當你意識到時它就是不斷的在你身上繞來繞去,所以就是好好的來面對它,我想那就是為什麼從少女須知開始,就覺得這個東西必須開始進行了。當然非常謝謝我的觀眾朋友,他們有跟上這整個對話過程,所以它才有一個契機可以發生。
Q3、如何決定這「殺龍工作坊」五堂課的主題呢?
A:這五堂課的主題,其實背後有一些幕後推手,就是關於去年少女須知在一個失控的狀態之下在思劇場進行演出,然後又進行了即刻重演等等,然後我就累積了一票女性主義伴侶,然後我們在少女須知的慶功宴的時候,隨便聊說一個完全沒有性高潮經驗的人如何透過學習而有性高潮,你覺得性高潮的預備動作是什麼?然後大家就提出了一些性高潮必備要有的條件因素是什麼,然後你就發現大家的需要都不太一樣,所以我就開始了一系列的關於女性性高潮經驗的訪談,之後就確立了這五個即將要開啟的工作坊內容。
Q4、這五堂課裡面,你最期待哪一堂課?
A:我其實本人真的有很認真的想了這個問題,因為我覺得媽的這問題真的是超難的,我其實當然每一堂課都很期待,因為我只要想到:「哇~我可能每一堂課要面對的夥伴都不一樣的時候」,你就覺得很像一個盲目的約會,然後就萬分的期待,感覺會有非常多火花產生。
但我個人可能最最最期待的(爆笑)就是當一個有性玩具的查某,因為那堂課就是要帶大家做線上購物然後就是要網路購物要買可以讓你興奮兩個禮拜的那個…就是玩具,我想說光是網路購物看到那個琳瑯滿目的,各式各樣不同指標的性玩具,然後又不同顏色的時候就覺得一定超有趣。我個人最期待就這堂。
說不定比收到禮物還更加有趣,因為你就可以有很多幻想,這個玩具可以幹嘛這樣子(大笑)哈哈哈哈好快樂喔~~~超久沒有買性玩具了,大概有半年吧,感覺我半年沒有買性玩具了,覺得需要買一下。我還會分享線上購物的重點,就是關於你如何辨別這個東西的品質跟它的價位(專業的)我是專業的因為我常常買。
Q5、從少女須知一直到這次的工作坊,有特別想要延續的精神或者是覺得這之間有什麼可以改變的部分嗎?
A:我覺得從少女須知到殺龍,我個人最想延續的一個核心的價值就是「關於女性作為一個個人主體」,有一件事情讓我覺得相當的不滿意,就是總是會說:「不在乎你是一個女性主義者,你可別忘了這世界上還是有男人跟女人的」。大家常常會拿性別,做某一種最後的手段來給你一個性別研究者的壓力,但對我來說完全不是一個問題,因為我想要提倡的就是女人你應該作為一個個人主體,當然你可以意識到這個社會裡有各式各樣性別的人,但是第一件事情最重要,你要做一個怎麼樣的女人?你得為自己負責跟決定,所以我最想延續的就是所有的女孩,我們都應該回歸到一個個人主體性上面去思考你的性別,而不是有一個比對,不是從你媽媽那邊比對過來也不是從你爸爸那邊,或者是從你的男朋友那邊,當然這最重要的也是因為我是一個個人主義者,我比較不是團體思考,我必須要理解我的需要是什麼,我要真誠的面對我的需要,當然這中間還是會有不免俗的一些溝通技巧,但是我認為看到自己的需要,理解自己的需要,並且知道自己有一些自己的權利在哪裡,我覺得是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很好的第一步,就是成為一個個人主體性。
除了個人主體性的就是,關於性自主、性自覺、就是你的性權。關於性權這塊我認為這是台灣最欠缺的,但同時也是我最能幫上忙的。因為我沒辦法當上勞動部長,去推動平權這款的法律,但是關於性學這塊,我有辦法,那是我所能盡到的,自己的微薄之力。然後想改變的是觀看模式,因為少女須知或多或少就是一個劇場作品,即便我試著在演出過程中找到任何機會與觀眾有個意念上、抽象上的交流,但是他仍然是有一個特定的觀看模式,它的確是有點模糊,但我仍然認為它是比較傳統的方式,它不會被定義為沈浸式劇場或是互動,即便我們有眼神的互動。
我覺得從少女須知到殺龍,關於共享的概念需要再提高多一點,這也是為什麽會想用,14世紀法國女性自主討論議題的概念作為工作坊主題,希望共享真的是共享,而不是我們講然後大家聽。但是這事情是需要大家一起幫忙的,因為如果只是我一個人很興奮的說我的玩具有多好當然也是很好,可是如果有女孩提出了問題,或者是有人提出他的使用心得,我們就是需要這個,因為我們需要有個機會讓女孩可以去聊這些東西,而且是在公眾場合,我覺得很棒。
Q6:我們很好奇這個工作坊會怎麼樣進行?你想要跟參與的學員一起創造出什麼嗎?
A:我覺得這個工作坊它對我來說它更是屬於「實踐」的可能性,我期待的是這個工作坊之後這些女孩們她會為她自己創造什麼事情?而不是我透過工作坊或創造一個作品,我認為我只能創造出點子,我不會透過工作坊創造出什麼,我覺得這之間是有差距的,我認為我我想要創造的一個東西叫做「女性主義特質」這事情非常有趣,就好像你如果看到一個男人,你可能會快的就會跟自己說:「喔他是個直男。」或者是「喔他就是一個gay。」可是你看到一個女人,你可能會說:「喔他是一個T」或者是「他是一個公主病。」那你有沒有可能有一個特質就叫「媽的它是一個女性主義者。」(笑)我認爲我是分辨得出來的,而且從走路就看得出來。你看久了你就看得出來,但為什麼我們現在還看不出來就是因為女性主義的特質沒有被激發出來。
所以這個工作坊的目標就是激發大家的女性主義的特質,然後我覺的它就會慢慢的帶來一些改變,雖然我真的不知道會花多久的時間,我只是覺得他對我來說就是我更想要繼續的,它長久看起來就會形成一個東西叫做「到底什麼是女性主義作品?」而且做為一個編舞,作為一個舞者,我常常在想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他們是怎麼說話?怎麼走路?怎麼跳舞?為什麼有時候一個女性主義者有娃娃音會降低對你的說服力?我不知道,我正在找,有一個有娃娃音的人成為女性主義者之後,他會變嗎?我覺得這是有可能的啊!就好像我在說中文跟我在說英文的時候其實我語調是落差很大的,孫安佐同理可證,但我覺得他是假仙(編:我也覺得)所以那個是我認為在抽象上面這個工作坊可能帶來的影響,或是這個工作坊可能創造出來的東西,它其實是一個抽象的女性主義特質,而不是一個作品或者是會有一個期末呈現,不會有這個東西,我覺得應該是會回到一個更全人的,而不單純只是,舞蹈作品或者是肢體動作,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提醒,我們要來練習一下,一個女性主義者可能的動作素材(笑),比如說用什麼特定的方式舉啞鈴,比如說一邊扭屁股一邊舉啞鈴,這好像可以去想像,蠻有趣的。大概是這樣。
Q7、未來品文會有其他相關的計劃嗎?未來在女性主義這塊上會想怎麼樣去推廣這個理念呢?
A:當一個女性她沒有性高潮的努力的時候,但是他又想像一個性高潮的時候,這個想像是虛無飄渺,不知道在哪裡的,所以它的可能性也很高,他跟任何男人做愛都有可能帶來他的性高潮,但這就是個問題啊,一個女人如果不會性高潮,他跟在座的男人做愛他可能也很難得到性高潮,可是他一直努力去試,認為有愛就會讓這個性更美好,對這可能會但不會讓他性高潮,就像你必須學習拿筷子才能把筷子拿好吃飯,就是一個日常的活動、日常的技能。
其實我有寫到一個重點,因為我最近在做假高潮的研究,我認為學會性高潮就是打破同溫層的一個辦法,因為我其實最害怕的同溫層就是有些女孩他們就會說:「如果沒有什麼,我也沒有關係。」比如說:「如果這個男生沒有要跟我交往,我也沒有關係。」、「我這次做愛沒有性高潮,我也沒有關係。」我就是想要打破這種事情,你知道全台灣女生的性高潮比例有多低嗎?超低喔。
但是在亞洲做這個研究我覺得有一個盲點是可能大部分的人他不敢說實話,他不敢說他有性高潮,或沒有性高潮,但我認為一半以上的台灣女孩是沒有性高潮經驗的,就是獲認識一些很優秀的女性藝術家,卻沒有性高潮經驗,他們已經25歲的時候,我蠻驚訝的,因為我想說他們最理解他們的身體的一群人,原則上來說他的精神跟他的身體連結的最好,可是他還是沒有,但是他們都仍然有一個固定的伴侶,這件事情讓我覺得很驚訝,然後我就想如果全世界的女生他都有性高潮,像對我來說有沒有伴侶根本不是那麼重要,而且當我考慮我的伴侶的時候我可能會從別的層次上去討論他,而不是跟他做愛的感覺,我覺得那對我來說就是如果台灣女孩性高潮的定義可以提高,當他再重新審視他跟另外別人的關係的時候他會有不同的層次,我認為這就是打破同溫層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因為顯然性高潮的比例並沒有提高,因為我們長久以來用一種特定的奇怪的方式對待彼此。
我們的性交就是男生的陰莖放進我的陰道裡,為什麼會有特定的符號就是口交一定是不舒服的,女生幫男生口交的過程就是被壓迫的,這都是一些很特定的刻板的印象,然後或者是為什麼每一次的被肛交都是女生,為什麼作為一個女朋友不能去肛交我的男朋友?其實有各式各樣的可能性在那裡,但是因為在這個社會風氣裡面,就是要去提供一個想像力,然後我覺得女孩能夠有更多性高潮。我身邊那些有性高潮的大部分的女生完全不會想要去跟男生花時間,因為投資報酬率真的太低了,我認為最好的對話是跟女孩對話。當女孩習得性高潮之後他就不會想要再花時間去跟那種沙文主義的男人在一起了,他們就出去市場外面了!希望啦!
可是我覺得跟傳統的女性溝通的方式,真的的確是非常的困難耶。
這題的確是非常的困擾我,傳統的女性就是會認為沒有性高潮也沒有關係的女性吧。
我覺得傳統的女性只會越來越少喔。因為你看時不時那個性別議題的對戰就一直在網路上開始,然後會造成那些中間選民就會搞不清楚,當大家困惑的時候就會去看更多的,他就會開始獲得各式各樣的資訊,所以同一時間我們要提供多元的選項,提供不同的理念,我媽媽是很傳統,我從來沒有問過他性高潮的問題,如果下一次遇到我可以當面問他一下,因為如果用賴問他他會打模糊仗。但是那時候他知道我做了少女須知,他問了我很多可愛的問題,比如他問了我說:「阿你的觀眾是男的比較多還是女的比較多?」就很在意我的觀眾人口的性別比例,我就說:「那媽媽你想看錄影嗎?」他就說:「我想看。」然後他看完也沒有說什麼,然後他也覺得很興奮,沒看過麻很好奇啊,但是回到性高潮這件事去問他,我覺得也有一點困難喔,所以我覺得在劇場裡面做一個工作坊是很棒的,因為在公共空間裡面去談論性,某種程度上有一個安全保障,這會比叫大家來蘇品文的家裡安全,因為他透過一個官方的或是一個學術的平台來組織,然後我覺得是健康的。就是跟保守派對話的方式吧,透過第三方。
「不是無法性高潮,只是還沒掌握到適合自己的方式。」為什麼第一堂課會是虛擬性伴侶,就是因為我想先從大家的想像出發,因為你的真實伴侶可能不會完成你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