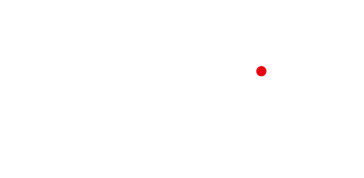文/林正尉
若說殖民、料理與勞動等三層次,不僅呈現某種宏大的遷徙軌跡,也再現出洗頭計畫「框外」連結的話,臺、菲兩地原如水平式的地圖/交集而成的耦合力,將時間與空間概念,如旋螺般、捲帶著具有「或已遺忘」的影響,那即上文所述的—曾有的歷史記憶;接下來的敘事與情境,我將垂直往返中山北路與金萬萬之內:
過去和現在,都有與他者相會的問題,這些他者正在旅行,也製造歷史。並且製造地理學和想像空間:……,處於一種和你的「此時此刻」的不同關係之中。 征服、探險與發現之旅,是有關歷史的、相遇的,不僅僅是關乎向外推進的 「跨越空間」。(Massey,2013:165)
Massey 所謂的時空碰撞,進而產生不同「此時此刻」的關係匯流;Jane Jacobs (2007:168)認為一座城市/街區在商業上的多采多姿,實與人口、景觀、文化機會和使用者的豐富性有關,以形成各種使用有效的經濟池聚。無論是 Massey、Jane Jacobs,甚至是作家王文娟筆下的「記憶綿延」,都明示了街道空間的可能生命。
日治初期,種滿六百棵相思樹的中山北路,不僅象徵著神聖的敕使參道,更是帝國權力控制本島的實質體現;戰後渡臺的蔣介石政權,將中山北路打造為象徵「美國—中華民國」於冷戰結構下的展演舞臺。
政治上的空間轉換,是透過拆解、破除舊朝治理表徵的國家神話營造計畫,如沿路的行道樹、建築、警察和車隊,不只肩負保衛國家元首與外交使館人員安全,還扮演「進步」與「現代化」的空間儀式。1960 年代初期, 13 個外交使館座落中山北路 的飯店與建築,近當時在臺使館數量的一半。使館、度假士兵、國際商業物流在此環繞不歇。此外,許多人避而不談中山北路所反映的戰後「東南亞史」,即反映中華民國在美蘇冷戰結構的地理戰略佈局:中華民國不僅是越南—美國戰爭的後勤基地,更與菲律賓、泰國等,合組美軍渡假中心,提供美軍休閒娛樂,滿足「勇赴沙場」前夕的性服務招待所。1974 年後,美軍撤離越南,日商開始進駐中山北路。且在 1979 年北投廢娼後,性工作者轉移至林森北路,條通區成為「洽商密談」的重要地點;此外,此區也是日商邁步「東南亞」區域,「享受」更多性服務的中繼站(參考殷寶寧, 2006:37-158)。
殷寶寧藉提出中山北路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強調陽剛、男性主導與政權表演的空間生產,旨在突顯(女)同志酒吧地景的浮現;不過,近二十年來的中山北路,累積四十餘間的攝影婚紗業,也是顯要課題。其可連結日治時期北門的相機業(今博愛路)、彼時臺北東區的田園時光、新興旅遊和林蔭大道規劃等「良好風景」,晚近連結中山北路上的異國情調氛圍、離外拍景點近,或因近五十年臺北商業的東移等影響, 促成愛國東路的婚紗業,「北移」中山北路的若干軌跡(金家禾、徐欣玉,2006;林芬郁,2019:123)。
還有,中山-大同區的髮廊歷史,也是值得討論的對象。在我而言,金萬萬的菲式髮廊,某種程度與臺北城中的理容地理學,產生親暱銜接。
2020 年 8 月 17 日因工作機緣,我曾拜訪光能里陳靜筠里長,詢問有關雙連捷運站周遭的髮廊故事。里長慷慨分享其家庭背景,正是赤峰街上「金雙連剪髮名店」的 經營者。她談論了 30 餘坪空間內,有著 20-40 多名洗髮小姐。顧客搭著火車,從羅東、 宜蘭等地慕名而來。她回憶起小時候:在髮廊感受的日常閒聊、大稻埕酒家小姐談情說愛,酒家女的身價再高,終要獨自面對夜晚失戀等悲歡離合。在她出身昔日髮廊的童時記憶之中,此地既是傾訴小道消息之地,美容師也是恪守秘密之樹洞。
且讓我們將視野移至赤峰街東側。戰後臺灣的理髮風格,深受上海與港式影響。 中山北路亦是外省籍中、高級官員的居住地。由軍政官員眷屬帶來的時尚潮流,使得理髮成為展示省籍與階級的社交場。徐瑩峰(2014:68-69)梳理 1970 年代後的理髮類型,探討毛髮於殖民與威權時代解放,於 1980 年代,再由香港美容師引入歐美與日本時尚,美學品味逐步取代舊有的上海式風格。中山站周遭髮廊,係以歐美日系為主。 有些人正是從髮姐、洗頭小妹轉為引介西方美學潮流的設計師,在 1980 年代後期逐漸興起美容商圈,而後帶動 90 年代鄰近百貨公司和服裝設計產業的崛起。
今日中山站的理容髮廊,不僅可見本地學徒,還有越南女性。我們可將「中山北路(外省中、高階級;上海與港式)—中山(香港;歐美日系)—雙連(臺式;平民)」視為一組攸關美容歷史的三角區域:它們曾分屬不同時代的社會階級與文化潮流,經學徒養成後,擴散各地;而「東南亞」區域人士進入臺灣後,也帶來自身傳統, 讓我們足以詮釋該區域文化在臺深耕的新面貌。值得一提的是,菲式髮藝與越南美甲,深具厚實的美國文化歷史底蘊。前者或多少讓「美國性」,重返中山北路上。
即便「洗頭計畫」、張剛華手上泡沫與日常閒聊,乍看之下微不足道,然正是這般微小的展演,才有能量牽引出極為寬廣的世界感。他的皂泡,有著深刻的時空交錯, 以及全球-地方感知的再詮釋能力,而後繼續連結「閒聊」的共通經驗,並使情感、 身體及歷史感知多重交錯;他與 Al 合作下的巧克力米塗鴉及手機直播,兩種媒介傳達截然不同的時空向度。
手機直播是另一種巧妙的在地選擇。它象徵著近二十年來,於全球移動環境下, 家庭與戀愛關係的內在變化特質。手機不僅用於聯繫遠方親人,更是跨越距離、感知親近,讓異地戀結所依附的影像與聲音,透過科技器具,傳達流傳已久的親暱。網路科技不僅是 21 世紀現代生活的基本特徵之一,帶來新的人際連結紐帶,這般世界感述說上個世紀的各種市場、國家、文明、文化、生活環境及人際間的界限逐漸褪去,也意味著生活中,將由此產生重要的全球性聯繫、衝突和相遇。無論是異地戀結、世界家庭、勞動市場、宗教變遷和重大危機,無不如此(參考 Beck & Beck-Gersheim, 2014:62-96)。
「洗頭計畫」跟隨個人及線上媒介之交換,進入各種異質身體、疆界與距離界限 正在迅速模糊的時/空網絡,進而滲透到他人「日常」。在此同時,與「洗頭計畫」 處於金萬萬大樓內的眾多限制和脈絡,產生極具張力的辯證關係。若說臺北版「洗頭計畫」使用的巧克力米,發生偶然的歷史鏈結的話,我們也可說:手機直播的呈現選擇,則是讓距離與親暱性在全球視野下重新切換,成為發生於當下愛情、親情與友情之外的視訊話題。這項計畫暴現於全球化浪潮底下,尋覓「變換座標」的軌跡與定錨。
五、自得其「移」:家居感、Chismis 與文化價值的在地傳承
先前奇怪她明明可以退休了,為何每天一定要坐鎮這家店?原來唯有在這裡,她才不只是個雜貨店老闆,而是個有求必應的萬事通。
–陳又津(2018/May/29)
陳又津曾在金萬萬訪問提供各項商品服務的菲律賓華僑。樓內不只供應日常所需,也是有時讓人坐憩、詢問水電修繕之處。
「萬事通」一詞,來自作家的描繪;歸功於計畫成員 Al,他也述及相似觀察: “chismis”,是「閒語」和「八卦」。Al 表示:選用巧克力米讓參與者分享想法,這般畫面似曾相似,彷若讓人見到菲國街上的占卜師(fortune-teller)。
陳又津記錄一部分何以「內聚」的場所精神,指認「建築物帶給場所的特質,這些特質和人產生親密關係」(Norberg-Schulz,1992:139),呼應了使用者是建築環境的重要一環。
適宜的「家居感」( home-making )和 chismis,是構成金萬萬內,難以言說或表述的雙重特質。彼此交雜。對菲國移民社群而言,適宜「家居感」不意味場地的物理舒適度。它們支撐起樓內各種擺設物的比鄰文法:緊湊、節奏、有機、便於納入主顧兩方抉擇的動線。
若說「洗頭計畫」是種展演計畫,我們就該談論其舞臺設置:看似蜷縮於二樓角落的髮廊內,然對該計畫的分析與評價,絕不能略過這些菲國社群的生活特質,因此不能忽視這些人、物、chismis 與聲音的密度。這般「劇場」評論之困難,關鍵在於我們如何檢視、閱讀其中的空間變化。流動的嬉鬧與嘈雜、炸著 Banana Q 的油煙、毛髮散落、理容時的蒸霧濃度與吹風機的熱氣相融,有時眼睛是睜不開的、雙腿常常要讓路,這才是真正構成「洗頭計畫」的舞臺性格。
店裡而外的穿梭人群,本身就是一個世界舞臺。在此,我們需要精準、有結構的舞臺分析:
第一層分析,著重移民的背景與傳統再生:菲律賓人生活在比鄉村、城鎮或國家更大範圍內的生活感之中,這種感覺,很少在大部分人口的日常體驗中消失(Kelly, 2000:1)。1994 年前後,「臺灣」不僅進入菲律賓海外移工熱門十大國家/地區第 4 名,僅次沙烏地阿拉伯、香港與日本,同時進入菲籍遷徙者的全球視域之中。「菲律賓人在世界上有家嗎?」James A. Tyne(2009:35)援引菲國社會學家 Filomeno Aguilar, Jr. 的重要名言,值得我們反思:遷入異地後,營造家居感不僅具有安定人心之積極作用,也帶來族群傳統傳承的可能,甚至是網路科技做為維持親暱關係的全球傳播形式,所「披荊斬棘」後的「文明路徑」。
第二種工序,是重新定義「家居感」。「家居感」使移民主體在不同地理位置之間,再度體驗與重新想像著「讓自己在家裡」的過程與感覺。另一方面,有別於傳統意義下具有守護、界閾、內在的「家庭」觀念,在被迫「無家可歸」的身體感知過程中,許多移民透過強調生物性、地理連結,和/或建立起跨越階級、地區、國家和種族界限的政治聯盟,來表達對「家」的需求和想望(Espiritu,2003:2)。
第三道分析:重新考量菲籍使用者的公共性。延續第一層分析的族群傳統和傳播,全球移民並未確實切分「現下的時間觀」,換言之,區辨何為過去、現在或是未來,本身並無太大意義。移民社群在意的是如何維持家庭、戀人與家鄉的親暱感,和族群之間的團結感。如前文所述:所有一切逐漸模糊其界限。
不過,移民社群(或移民所在之處)與城市,生活之中具有類似的特質,那即是 「全球地方感」。根據亞洲新情境,我認為要適時調整 Svetlana Boym(2010:86)的觀點。她認為「地方世界主義」並不建立於電子界面的聯繫上,而是在一個物理空間中的陌生人相會後的跨文化邂逅。至此,我們要考量移民主體的立場:移民主體所在的城市或區域,也有其自身的中心與邊緣。
菲律賓移民社群的公共性為何?其中一點,已有許多學者研究過的,包含家庭感的維繫、信仰維持、海外自助團體與機構,都有可能讓原生家庭之鏈結變得浮動。如 Watanabe 與 Hosoda(2016:92-113)探討阿聯酉的菲律賓移工的改宗狀況:他/她們在異地放棄原生家庭的宗教價值,皈依較能獲得社會支持的信仰勢力,是一種「具有浮動、轉變特質的親暱/公共性」例子;還有一種是移民社群空間使用的再製模式,涉及族群傳統的異地移轉。Ramos(2007:237-254)研究馬尼拉區域規劃之下,平民生活紋理不斷經歷消失、復甦與移轉等過程。Ramos 認為小型雜貨店(sari-sari)的自我再生能力,有效填空傳統都市規劃的漏洞。不單如此,都市規劃須與平民百姓的習慣站在一塊:菲人會將互相競爭、提供同類商品的店舖並列一起:
⋯⋯非常有效,這是由菲律賓人的心理和消費者的普遍心理決定的。菲國購物者通常喜歡在決定消費之前,先逛一下,從一個店家蹦到另一個店家,會買得更高興、更有收穫。(ibid., pp. 245-247)
金萬萬大樓的裡外,我們容易體驗到物品與店家的同質性。我們也可視為某種面臨消失、復甦與移轉的過程,只是國家/地區不同罷了。基本上,菲國海外勞動者繼續傳承某些共有的生活節奏,不單如此,還承襲某些前殖民時期遺留的社群交往習慣。這也是臺灣人與菲國社群往來或合作,必須注意的面向:
- kapwa:集體性、連結感,即使互不相識的菲律賓人也能寒暄。
- utang ng loob:感激之債,以促成更多的互助形式與報答行動。
- hiya:家庭榮辱與共的羞恥感;個人舉止即代表家庭形象。
- pakikasama:重視人際相處的情緒平衡與寬容,追求和諧、避免衝突。
對菲律賓人言,構成 Bayanihan(社區/群)的重要因素,在於尊重上述四種前殖民時期之後,持續保留至今的交際美德。無論是國內抑或海外,這樣的集體主義和社群意識,都重視「為共同利益而共同生活和工作的能力」(Nadal,2009: 43-46)。
最後一道分析,則是理解離散的親密。Boym(2010:281-282)對該詞的描繪與洞察,值得再三反芻。其見解,適用於我們面對「洗頭計畫」中的親密分析:
「離散的親密」只能透過間接或暗示、透過故事和隱密來接近。⋯⋯並不允許某種無介質的情感融合,而只允諾某種不穩定的溫情——雖然同樣深厚,但意識到了自己的暫時性。和具有透明性、真實性與終極歸屬的親密烏托邦形象,所形成的對照是,離散的親密在定義上是有錯位性質的。
離散的親密,根植於對家園土地的縈繞、疑慮、希望和嚮往,是重要的公共性。 正因短暫相遇,如同洗髮的泡沫,化作彼此之間的介質,何嘗沒有人向團隊傾訴真實情感呢?嚴格來說,「洗頭計畫」先後經歷大稻埕的展演實作,於今年歷經中壢與臺北的社群接軌,最大突破在於「體察他者的公共性」。而這些公共性總是以複數型態出現的。計畫團隊於各種人際往來之間,辨識店家與身體的活動界閾;同時,為讓自己避免成為不必要的存在,自發學習一些 Tagalog 語,以協助他人;或消費、參與店務勞動。身分如此切換,到最後,或許是為了證明一件事:
「此時此刻,我們就在這裡」。
六、朝向沒有小結的終點:是多元文化,還是重返日常生活敘事?
Dito na Tayo. ——「我們來了」(一則出現在金萬萬內的廣告標語)
最終要傳達的,莫過於在一個隨時隱藏「敵人」的世界,藝術仍是值得我們想像、 模擬「大敵」現身的長槍,儘管它做為實體革命的作用仍有些無法為之的距離。 然而,我們要理解的是,在當今藝術實踐的世界裡仍存在著唐吉軻德式的營造者, 騎著瘦馬、衝破風車,嶄露直殺「大敵」的力道與衝勁。如果還有這樣的人與作品,我願當個僕人桑丘,勇於見證且記錄這份只有藝術能提供出的感性、且要不斷感謝「大敵」「現身」的熱情。
–林正尉(2015:447)
照理說,是該進入終點了。
與其說結尾,不如視為觀察員的反身表述或補遺。
五年前,在我取得戲劇碩士學歷後,首份工作便是擔任《四方報》記者。至今, 我累積些許「東南亞」相關的文化工作機會,包含本次「在臺印、菲社群生活文化交流計畫」。
五年前,我因「太陽花運動」而停止從事劇場書寫,將研究領域,專注投入不同城市、社群的自發表演歷史;這些影響與養分持續至今,甚至有所轉化:我持續發問全球遷徙的移民和勞動者們,其自身對「表演」或「藝術」的定義方式會是如何?
我尤為鎖定 2010 年以降,迄今十年來的移民表演型態及其基礎。如第二篇開頭談到:移民女性與勞動者,漸從警政、衛福、社福與勞工局處的身體治理—照護技術, 部分移轉至文化部門,得到新的發展資源。曾經,除了少部分有著草根及議題倡議的團隊(如南洋姐妹會及其「南洋姐妹劇團」),然在地方局處的想像與視域,料理美食依舊、「母國情調」的文化想像為主,或一貫的、被動員演出的客體對象。
幾年來,我們可以樂觀發現,一些移民女性和移工團體,或多或少在不同協力系統下,轉向思索主體的定位:仍保持部分自發性的菲國移工選美比賽、跨區體育運動賽事、或「科地雷拉日」;一些「私—公」協力所辦理節慶如「卡蒂妮日」、「印尼國慶日」、潑水節和菲國天主教節慶等,甚至新移民女性領袖人物引領的策展實踐 (如阮金紅等);再加上更多的臺灣青年(包含「新二代」)投入相關倡議、文化創新與組織行動,足讓人開創新的期待與想像。
本系列文章中的主角:兩年來,在大稻埕的 Thinkers’ Studio 連結朝向「東南亞」、 杜彥穎等人「印尼坤甸—她的娘家是我們的冒險」、張剛華返回印尼山口洋尋找自身家鄉連結及其創作發展可能等,可謂較年輕、活力的組成。他/她們的歷史包袱較少,且有著能對特定議題提出新視野、具想像的實踐特質。
若循上述脈絡,2020「洗頭計畫」仍可從臺灣表演藝術發展歷程檢視之,倒也有些獨特意義。從「南洋姐妹劇團」訴諸的自我發聲和議題倡議,或「臺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尋找露西亞》秉持的教習實踐立場等,這些社會意義鮮明的表演團隊存而不論。我的立場在於:2020「洗頭計畫」所求的日常實踐,與在正規劇場之中,展演 「新住民議題」這件事,實存著值得區辨的深層意義。
說實話,當我還在純劇場生態認識「新住民的動員與展演」,會覺得它新、有時代意義;不過,我曾對報社同事在《四方報》辦公室內,多少因時常接到劇團或演藝機構致電找演員的過程(並且提出要符合的外在姿體模態)額外花費力氣,是看在眼裡的。對我來說,我寧願為打電話來報社的泰國移工,努力協助他們洽談大學裡的運動場地,好讓眾人期待已久的跨縣市足球聯誼賽得以發生。這是讓我時常反省的事。
即便稱之為實驗劇場或更多的正規劇場,提供的「安全」表演環境,仍涉及視線的權力配置:我們(持票進場的觀眾)依然在這個安全的空間制度內,觀看新住民 (或故事)如何動員的姿態與過程。我並非全然否認劇場對該議題的推廣,我認為 「新住民身分進入『劇場』展演」確實有其原本的美意,然須抱持「權力存在其中」 的自我察覺。它最終不會只是一場作品。它透露姿態、展演與權力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生產。要是忽略其從政策、計劃書構造、實得補助、誰能簽收薪資領據、劇場空間、 文本(多半涉及作者的再詮釋)、導演位置、演員遴選機制與舞臺技術裝置等⋯⋯所架構而出的「一部作品」,其原有的善意,同樣也會造成自身的矛盾。
我不是藝評人,不必操趕著一場復一場的評論作業,無心探討「洗頭計畫」優劣, 或該賦予的評價。不過,我也同意不會有人就這樣的日常觀察,提出與現有政策、藝文環境、身體政治或歷史意義等,如此龐大的書寫計畫。三篇文章所構成的書寫計畫, 篇篇都有其要面對的目標及作法,而我最終要指出:若無法啟動「嘗試挖掘不同合作群體的公共性」的信念,我們其實無法體察如此日常的洗頭展演, 它的深度、廣度何在(必須註明:創作團隊也不知情)?或提供什麼樣的類藝術想像?
書寫計畫的核心意義,就像釣客站在池潭畔的某個定點,一連貫投擲釣竿、魚線、 浮球,滾動手上捲線器那樣,一串弧形動作。書寫可以丈量的,是描繪釣者拋出魚標的滑動軌跡,及貼近池水的波紋。但對於什麼魚?牠們為何而來?方向?深度幾米、 暗流範圍,這些關鍵知識和抉擇,仍在於釣客的思維之中。
這三篇文章和意義,如同唐吉軻德旁的僕人桑丘:專注記錄一些能將日常轉為幻想的世界移動者圖像,與他/她們何以能「此時此刻」交會的複影。
今次「洗頭計畫」,有別 2019 年在大稻埕國際藝術節的「內向性」。如我說過的, 中壢場的「洗頭餐車計畫」,讓兩組團隊攜手展開跨地合作的可能;臺北場的實驗, 則是如何自我學習一套體察菲國族群的生活方式。後者專注觀察、操演著「讓自己進入一個陌生場域」中的社會紋理。為了支持張剛華在理容院內的洗頭實踐,計畫成員投入觀察店家間的互動與個性、學習叫賣、互助協力,得以協商出一種暫時被接受的立場與狀態。這種受到移動者接受的條件和儀式,無疑是個新嘗試:我們成為被(相當自然)動員的對象;我們被觀察、八卦、被打鬧。
主體是互換的。這讓「洗頭計畫」的社會意涵與公共性,成就出值得註記的歷史定位。尤在 2020 年全球瘟疫影響下、臺灣「新南向」政策的發展架構等,顯現積極的意義。人類的遷移畢竟是多向的,對許多菲籍移動者而言,臺灣充其量,就是個中繼點;但對中壢的印華媽媽們不是。當我們平心探討「社區/群營造」、 「主體」、 「東南亞」、「文化展演」等⋯⋯,又該如何力求突破自身認知/行動限制?
該如何思考多重主體或互換主體的藝術性?是下一個十年,持續重要的發問。我們不需多大、多麼動聽的辭藻,即便口號只是促成人們不要忽略某些事罷了。當我們不用再談「多元文化」的那一天起,真正民主、平等的多元性才將真正落實,證明它已潛入人們的基本生活,不需再三提醒。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場長時段的日常革命。
今年的「洗頭餐車計畫」,無形之中埋下這顆值得珍藏的種子:透過杜彥穎團隊協助,我們得到印華媽媽們的更多支持;也透過 Al 合作參與,我們逐步接收自菲律賓社群的包容與理解。重要的是,某種程度而言,他/她們視我們為自己人,甚是久違的好友;重要的是,「我們」與他/她們的話題,有超過 80%內容,環繞於其家鄉、 島嶼、村莊、家人等故事。就如杜彥穎等人與母親們學習、紀錄料理,相處宛若家人;而張剛華與 Al,轉身,與正在美髮的客戶閒聊:
「所以啊,Ganda(髮廊)對你/妳而言是什麼呀」?
我注意到:她們閉著眼,全然感受按摩的力道,或笑著透過鏡子反看我們,咧笑說:「好奇怪的問題哈。沒什麼啊,我習慣來這裡,想讓自己 ganda(美麗)耶」。
彼此話題不是圍繞臺灣,不是自己國家。不是認同。不會是「東南亞」、「新南向」,和受到標籤的這群人、乾淨的那群人;是島嶼、家庭、孩子、愛侶,與「我快回去了。你們之後要不要來宿霧我家玩」?
這聽來是極度遙遠的邀約,就只是在當下,我們開始有著同心的友誼。
一種極為日常的關愛與發問。
透過肥皂泡泡與日常言說,來傳遞親暱,如此看來才是彼此關係解構與重新組構的契機。
參考資料
Amrith, Sunil 著、堯嘉寧譯, 2017,《橫渡孟加拉灣》,臺北:臉譜。
Anderson, Benedict 著、徐德林譯,2018,《椰殼碗外的人生》,上海:上海人民。
Bauman, Zygmunt 著、姚偉等譯,2018,《門口的陌生人》,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Beck, Ulrich & Beck-Gersheim, Elisabeth 著、樊榮譯,2014,《全球熱戀:全球化時代的愛情與婚姻》,北京:北京大學。
Berger, John & Mohr, Jean 著、劉張鉑瀧譯,2019,《第七人》,杭州:中國美術學院。
Boym, Svetlana著、楊德友譯,2010,《懷舊的未來》,南京:譯林。
Cannell, Fenella. 1999. Power and Intimacy in the Christian Philippin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mcke, Carolin 著、郭力譯,2019,《何處為敵》,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Espiritu, Yen Le. 2003. Home Bound: Filipino American Lives across Cultures, Communities, and Countries. Berkeley &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omily of Holy Father Francis. 2013/Jul./8. “Visit to Lampedusa”. Retrieved from http://w2.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homilies/2013/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130708_omelia-lampedusa.html (瀏覽時間:2020 年 9 月 3 日)
Jacobs, Jane 著、吳鄭重譯注,2007,《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 啟發》,臺北:聯經。
Kelly, Philip F. 2000. Landscapes of Globalization: Human Geographies of Economic Change in the Philippines. New York: Routledge.
Ladurie, Emmanuel LeRoy 著、楊豫等譯,2002,〈一種概念:疾病帶來的全球一體化 (14-17 世紀)〉,收於《歷史學家的思想和方法》,頁 35-110,上海:上 海人文。
Massey, Doreen 著、王愛松譯,2013,《保衛空間》,南京:江蘇教育。
Nadal, Kevin L. 2009. Filipino American Psychology. Indiana: AuthorHouse.
Norberg-Schulz, Christian 著、施植明譯,1992,〈場所?〉,收於 Husserl, Edmund 等著、季鐵男等譯,《建築現象學導論》,頁 121-140,苗栗縣: 桂冠。
Ramos, Grace C. 著,司玲、司然譯,2007,〈菲律賓的多維規劃和公共空間〉,收於繆朴編著,《亞太城市的公共空間-當前的問題與對策》,頁 237-254,北京:中國建築工業。
Rodell, Paul A. 2002. Culture and Customs of the Philippines. Westport & Connecticut & London: Greenwood Press.
See, Sarita Echavez. 2016.“Hair Lines: Filipino American Art and the Uses of Abstraction ”. In Manalansan IV, Martin F. & Espiritu, Augusto F. (ed.). Filipino Studies: Palimpsests of Nation and Diaspor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p. 297-312.
Sassen, Saskia 著、黃克先譯,2006,《客人?外人?遷徙在歐洲(1800~)》,臺北:巨流。
Sontag, Susan 著、刁曉華譯,2000,《疾病的隱喻》,臺北:大田。
Tyner, James A. 2009. The Philippines: Mobilities, Identities, Globalization.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Watanabe, Akiko & Hosoda, Naomi. 2016.“ Transforming Intimate Spheres and Incorporating New Power Relationships: Religious Conversions of Filipino Workers i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In Um, Khatharya & Gaspar, Sofia (ed.). Southeast Asian Migration: People on the Move in Search of Work, Refuge and Belonging. Brighton & Chicago & Toronto: Sussex Academic Press.
Welsh, Jennifer 著、魯力譯,2020,《歷史的回歸:21 世紀的衝突、遷徙和地緣政 治》,南京:南京大學。
Whyte, William H. 著,葉齊茂、倪曉暉譯,2016,《小城市空間的社會生活》,上海:上海譯文。
王文娟, 2010,《微憂-那些無事在台北走路時想起的小事》,臺北:印刻文學。
吳象元,2019/Apr./2,〈【印尼大選】4 月 14 日海外投票全台設 34 處投票所,讓他們:為故鄉投下選票〉,「關鍵評論網」。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6579 (瀏覽時間:2020 年 9 月 6 日)。
金家禾、徐欣玉,2006/3,〈影響創意服務業空間群聚因素之研究— 以台北中山北路婚紗攝影業為例〉,收於《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13):1-16, 臺北: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林正尉,2015,《鏡縫拾荒 展演地圖:從巴黎公社到飛夢社區》,臺北: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芬郁,2019,〈論臺北市攝影產業地景之變遷〉,收於臺北市立文獻館編《第八屆臺北學: 城市前世到今生-臺北考現學》,頁 106-141,臺北:臺北市立文獻館。
段義孚著、潘桂成等譯,2008,《恐懼》,新北市:立緒。
思劇場,2019/Aug./16,〈大稻埕國際藝術節-洗頭:跟我說一個故事!〉。https://www.tkstheatre.com/event/2019/7/16(瀏覽時間:2020 年 9 月 7 日)。
殷寶寧,2006,《情慾.國族.後殖民-誰的中山北路?》,新北市:左岸文化。
徐瑩峰,2014,《台北市中山雙連街區創意群聚的權力幾何學》,臺北市: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又津,2018/May/29,〈金萬萬大樓的前世今生〉, 「鏡週刊」。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80525pol008/(瀏覽時間:2020 年 9 月 7 日)。
陳又津,2018/May/29,〈雜貨店裡的萬事通〉, 「鏡週刊」。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80525pol009/ (瀏覽時間:2020 年 9 月 8 日)。
Summary
Proofreading|Melody Wagner
Compared with the experience of co-operation in July, Taoyuan City, the experience of the “Shampoo Project ” (Taipei-based version) is a chance indeed to re-practice and consider the meanings for engagement, and the meanings to perform in the Filipino public sphere. Thus, the members are required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local Filipinos who first moved in nearly 20 years ago in such a department store that used to sell imported goods.
Within the narrow corridors and the hair salons in the building, the members need to learn how to discipline their bodies, and behaviors, also observe actively about the surroundings, and learn Tagalog for supporting other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iscuss how the “sense of everyday life” of the “Shampoo Project “being shuttled back and forth the domestic Filipinos in the building, as well as the Taiwanese (outsiders; guests). The world is a stage. As Shakespeare mentioned, this article combines the cultural memory which is co-shared by both, show that how the project members re-learn and respect the Filipino traditions which are being proceeded through their tribal values: Bayanihan, being in a sense of community through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