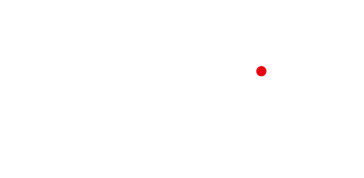文/林正尉
饗宴與洗髮(3):全球視野下的泡泡隱喻
⋯⋯我們生活在肥皂泡泡中。無論這種肥皂泡多麼漂亮,都是虛幻的;它們提供短暫、空洞的幻象;導致我們對他人冷漠;是的,它甚至導致冷漠的全球化。 —Homily of Holy Father Francis(2013/Jul./8)
2013 年 7 月 8 日,教宗法蘭西斯一世拜訪地中海的 Lampedusa,針對全球移民現象導致的苦難與冷漠,號召人們重省自身的道德恐慌與選擇性忽視。皂泡象徵著稍縱即逝的幻象,是浮沉於海洋與時勢的身體寓意。這種隱喻,回應社會學者 Zygmunt Bauman(2018: 6)引用 Robert Winder 的評論:「我們仍可按照我們的習慣,抽把椅子坐在沙灘,對洶湧而來的浪潮嘶吼,但海浪不會理睬,大海也不會後退」。
荒謬與徒勞。泡泡像隔膜,尤對遷移者而言;關心全球移民的人多,卻不斷呼喊著警訊。如今,又該如何面對這般處境?
早在上世紀的 1970 年代,藝評家 John Berger(2019:41)於其著深刻的歐洲移工敘事,業已提及:放棄隱喻吧。移工的遷移,像別人夢中的行動,然其意願滲透著歷史必然性,「無論是他還是他遇到的任何人,都意識不到這點。這也就是為何他的生活就像是一場別人的夢境」;隨全球民粹主義與移民潮現象劇增,加拿大學者 Jennifer Welsh(2020)不甚認同 Francis Fukuyama所言:自由民主是是人類意識進步的終點。她認為衝突與不義於今愈演愈烈。歷史不曾終結,只有回歸。
那麼,有什麼做法來正視虛幻泡沫呢?
Saskia Sassen(2006:7)試圖定義「今日的定居者」概念:老舊的歸屬概念,不適於理解今日複雜脈絡解。此時此刻,我們已不能再將起點及終點的區分,等同於對他者的歸類,國界不再將人類的存在狀況區分開來;往返戰地的德國記者Carolin Emcke (2019:169)指出:理解「移民社會」的真正意義在於,「將移民及其子孫僅是為公眾討論對象的時代終於結束了。我們需要一點時間理解,所有⋯⋯也是公眾討論的主體」;且如 Bauman(2018:19-20)所見,當今「一個地球、人類一體」的 現實挑戰,並非不斷強化疏離。與之相反。人們應尋找、建立起密切的接觸機會和更為熟悉的關係。首要障礙就是拒絕對話的姿態,「拒絕對話往往源於(同時促進)自我疏遠、相互離心、熟視無睹,總之,是源於冷漠」⋯⋯。
那怕仍待一段漫長且坎坷的時光。
一、序曲 (1):雙面觀察員
身為計畫「觀察員」,激起我重新檢閱、思索教宗言下的泡泡,究竟意味著什麼?
「洗頭計畫」從中壢移轉到臺北「小馬尼拉區」(晴光市場-聖多福教堂周遭), 時逢 2020 年 7 月底。衛福部疾病管制署於 7 月 24 日正式公告菲律賓 COVID-19 確診率僅次中國大陸。 「沒事就不要去。你沒看新聞嗎?」家人是從媒體獲得菲律賓的疫情資訊,再從 Facebook 得知我正參與這項計畫。
他們看到更多畫面:是我的照片、團隊的直播。我們透露自身穿梭於菲律賓人經營的髮廊。「(你們)好像一點都不怕似的」。
我與菲律賓社群相處在一塊。因此,我被觀察著。
家中成員的評斷與擔憂,想當然耳;我們以為的日常,是普遍人的恐懼。流行病傳播與全球移動與親暱成正比。環保運動風起雲湧的 1970 年代,已有人就歷史研究成果,嚴正警告疾病「全球一體化」將伴隨航空而播散(Ladurie,2002:35-36);流行病誘迫人們注意來自世界各地的敵意,此話進而呼應段義孚(2008:160-183)筆下的恐懼空間。傳染病的世界裡,人類本身就是恐懼的主因:
對身體健康的人來說,生病的人不僅是邪惡的受害者,而且也是幫兇。就算傳染病並未製造一種恐慌與懷疑的氛圍,在彼此關係密切的社區裡,又是在未經公開承認的社會緊張下勞動,縱使號稱只有少數人生病,患病仍然可能引發最深的深沉的敵意。
不少人將族裔地景視作「飛地」(enclave):前者包含遷移的現實與幻想;後者涵蓋政治管理的譬喻。近期「飛地」的鮮明案例,是 2019 年 4 月中旬,遍及臺灣各縣市的印尼總統大選投票所,由 34 處小吃店與雜貨店組成(吳象元,2019/Apr./2),足見更多全球政治何以傳播的可能。然而,疫情流行全球的當下,讓這些原本就可能受到鄰里排斥的區域或單位,更蒙上陰影,宛若「疾病王國」的海外領地:
「與那情境相關的幻想,不是疾病真正的樣子,而是人們對它的想像」(Sontag, 2000:9)。
二、序曲 (2):愛美文化的遷移與政治
相較中壢版「洗頭餐車計畫」合作的印華母親社群,臺北版有著截然不同的討論方式。除了疫情陰影之外,當計畫團隊進入「小馬尼拉區」,將面對的是冷戰殘餘、 族群遷徙、都市建築的時序銘刻,與更大範圍的全球都市規模變遷等面向。
另一方面,張剛華手中皂泡,和金萬萬大樓(以下簡稱「金萬萬」內)的 「Ganda」菲式理髮廳,合力拉出某種別於教宗所宣示的涵義。
小從毛髮體膚養護,大至選美競賽,在菲律賓審美文化裡,這樣的身體意識是建立於一連串信仰榮耀、殖民歷史、國族思維,進而抬高到全球視野。自理髮廳、移工選秀到世界小姐選拔,我們都可看到相似路徑:首先,菲國選美競賽,可追溯西班牙殖民時期的天主教傳統,結合神聖性與世俗感。富有家庭為女兒辦理的婚禮選夫,徵選的不只是俊美或華麗的伴侶,為教堂奉獻金額高寡的人,才是選拔贏家的關鍵;美國殖民菲律賓之後,引進智性、美麗、菁英與品味於一身的「環球小姐」形象,融入新類型的選美競賽(brains and beauty lang);再則,審美感知與文化產品有關。由美國文化輸出的電影工業,在都會與城鎮傳播。Tagalog 電影粗分 mapangisi(讓人咧嘴 一笑的鬧劇)、 laban(具衝突色彩的武打片)跟 drama(戀愛戲碼、家庭故事或大眾鄉土劇),不同類型的服裝及影像經驗,都能帶動閱聽者的感官與認知。不僅如此, 在影劇不易進入的鄉間,人們聆聽廣播劇。廣播肥皂劇同樣塑造 magayon(美麗)和 guapo/boki(英俊) 等意識,或穿著得體的教學指南(Cannell,1999: 203-206)。
在菲國,「愛美」文化的實踐與養成,具有「神聖—世俗」、「都會—城鎮(如 town fiesta)—鄉間」、「歐美亞移植—菲律賓生產—全球播散」等時空移轉的特徵。
三、歷史-空間親暱性(1):殖民、料理與勞動
托歷史教育之幸,人們對西班牙治理北臺灣(1626-1642;涵蓋今日臺北地區)時期,或許不再全然陌生。有趣的是,我們對「東南亞」及早期福爾摩沙的互動關係, 鮮少在當前「東南亞熱」的社會氛圍裡,有效檢驗、融合或提倡。我們甚少討論17世紀的菲律賓人來到淡水做什麼?印度馬達拉斯薩拉森建築,與淡水紅毛城的樣式關係為何?淡水外國人墳墓中為何葬著錫蘭人?英格蘭商人必麒麟(William Alexander)筆下,在淡水發生海灘、或是驅趕反對建立洋行的漢人的印度人群像;或是馬來水手燒殺臺南、高雄一帶漁村的歷史記憶,帶進本土的思考脈絡。
我們似乎忽略Sunil Amrith(2017)於《橫渡孟加拉灣》的基本提醒。他提及拿破崙戰爭、荷蘭東印度公司破產、英荷「倫敦條約」、二戰「東南亞」戰區及民族國家興起,種種因素使得「南亞」與「東南亞」受到戰略式的切割。跨歷史、政治、地域的全盤思考,失去了該有的世界輪廓,使得現代「區域史」、「國別史」劃分,讓我們更難理解曾在19世紀臺灣土地上,為何出現錫蘭人、印度人和馬來人等情狀。
著名「東南亞」學者 Benedict Anderson(2018:59)的自傳亦談到:「倘若體制性的『東南亞』概念不存在,⋯⋯菲律賓則可能隸屬於拉丁美洲研究」。他闡明「東南亞」一詞深受戰爭、學科研究與政治佈局所塑形,此一概念,暗示某種集體性(而這種集體性是難有共識的)。
正當臺灣普遍將菲國視為「東南亞」一部分,我傾向不這麼做;也正因菲律賓與早期福爾摩沙,共享一些拉丁美洲式的「歷史」殘餘,使得前者的文化涵意在本文、本地的脈絡裡,都能重疊。
美籍菲裔雕塑家 Reane Estrada,曾以「毛髮雕塑」抵抗美國人視其母國為:缺乏文化底蘊、僅擁抱殖民遺產的「原始東方主義」(primitivizing orientalism)(See, 2016:300);儘管張剛華的洗頭展演,並未清楚意識其有歷史意義(具有再詮釋的特徵),或不含任何抵抗意識,然我觀察 「Ganda」髮廊的人際相處模式之後,發現其中的語言學習模式,不斷切換:從中文、英文、Tagalog,偶爾共學、穿插臺語、西班牙文及義大利文等歐陸語系。各種語言混雜摻入對話中,來增進彼此理解及熟悉。其中的西班牙文,本來就附著於拉丁美洲、菲律賓與北臺灣的治理傳統。可以說:Reane Estrada與張剛華的藝術展演,不約而同讓「菲律賓」及「臺灣」的主體概念相互漂浮。 前者透過抵抗,消緩「菲律賓」一詞的美式偏見;後者則是透過打鬧、閒聊與洗頭之間,以親暱協作等細微過程,讓「日常」貫穿某種「世界觀」的宏大歷史敘事。
在張剛華安排下,向菲國洗頭參與者詢問「想留的文字、想畫的圖;或,對你/妳而言,『Ganda』髮廊是什麼?」不同於中壢版「洗頭餐車計畫」,以鹽巴讓參與者留下「文獻紀錄」,他最終在臺北版選用彩色巧克力米做為替代。
語言的浮動狀態和巧克力米,是讓本文書寫,導向世界—歷史思考的關鍵。換句話說,張剛華的美感選擇,或如此臨時的偶發及決定,反變成一組具影響力的轉換器:讓本文中的菲律賓—東南亞脈絡,轉為空間尺度更大的歷史論述,繼而包覆了 Anderson 論及菲律賓的拉美研究意識,和冷戰政治分析等因素。
從視覺經驗看來,繽紛的巧克力色彩,令人聯想起西班牙殖民政治與天主教的歷史;另外,巧克力米進入臺灣,則因 1960-1970 年代,美國向國民黨政權大量輸送麵粉產品以求牟利的交換條件,尾隨麵包烘焙業進入島內的歷史過程。髮廊外的巧克力米,連結金萬萬內的麵包銷售服務,加上樓內充斥、漂浮西文的料理名,諸種複雜且動態的感官經驗,醞釀出朦朧的歷史—空間圖像,直指中山北路曾經雲集的使館意象。
西班牙軍隊殖民拉丁美洲後,繼續前往菲律賓等地,帶入食物、物品命名與勞動制度。透過一些傳教士紀錄(如 Fray Juan de los Angeles 神父),我們可見證 17 世紀的北臺灣亦是如此。如今,菲籍遷徙者為臺北捎來新的時空層疊。
金萬萬周圍常見的菲式菜餚,像是燉豬肉(adobo)、乳豬(lechon;西文 lechón)、酸湯(sinigang)、醬肉(menudo;西文 mechado,常以 mole 醬淋於肉上), 而貨品如手錶(relo;西文 reloj)等⋯⋯,它們共享了移動與殖民歷史的常民資產;菲式餐車(street vendor)與攤販,聚集大樓內外的人行道上,於周末兜售糕點、冰淇淋(如 ice candy 和 halo-halo)、水果(如香蕉;saging)和鴨仔蛋(balut)。餐車, 也是西殖時期的日常產物(Rodell, 2002: 109)。
還有甜點。菲律賓邦板牙(Pampanga)地區以甜點聞名,是因西班牙—美國殖民時期,留下具規模的糖廠建設和無數看不見的工人(ibid., p. 104)。我們在金萬萬仍可看到大量甜點,可別忘了,在 17 世紀西班牙治理北臺灣時,被迫徵集的傭兵、建築工和奴隸,在此修築起城堡、房舍和修道院,部分人士就來自邦板牙與呂宋島東北方 的卡加揚谷地(Cagayan Valley)。在此,即便是今日金萬萬周遭攤車的甜膩糕點,或搭著捷運遊覽淡水紅毛城,我們反覆與三百年前的勞動者身影交錯著。
總之,當張剛華開始採用巧克力米做為參與者的展演物件時,意義有所轉化,不再是他原所認知的日常洗頭展演了。冥冥之中,自他閱讀當地文化紋理後的物件抉擇, 開始變成整場展演的重要「行動者」(agents)。「行動」是多義的。它們互相擾動出更為廣闊的閱讀層次:拓展臺灣與菲律賓兩地,在殖民、料理與勞動等三層次中,所展演、導向(directing)歷史—空間親暱性的各種可能。
四、歷史-空間親暱性 (2):中山北路的愛與愁
即使個人的旅程必定面臨終結,但更多的出發還在繼續。中山北路勢必還要再長,長過了它自身所能欲望的樣子,長過了記憶的邊界。
–王文娟(2010:59)
我曾參與 2019 年《洗頭:跟我說一個故事》(大稻埕國際藝術節);2020 年, 我以「觀察員」身分加入該計畫。2019 年於大稻埕「 豐味果品」中庭「上演」的「洗頭計畫」,是一尚屬「安全」的空間。行政人員於「藝術節」執行架構下,引導參與者進場、宣布時間,而人們一一目睹安排妥當的椅凳、梳洗器具擺設和站好的美容師 (「演員」)。這是設計後的場景,讓藝術家專注於「體驗、交換、執行『洗頭』,重新認識這個日常行為在當代文化、地方社群與個人之中隱含的現象與故事文本」 (思劇場,2019/Aug./16)。
會後,張剛華曾問我:「『社區劇場』是什麼」?至今這問題仍使我印象深刻。 即便略知臺灣近三十年的「社區劇場」進程,也了解「洗頭計畫」演員們進入髮廊 「實習」的工作方法,我當下仍是失語的。「社區」與「劇場」總是多義。倘若我們不曾就多種組合進行分析、或將「社區/群」問題有所指引,任何一種發生於大稻埕街上或果品店(無論多麼親近民眾的空間)的「演出」形式,論及內容或指涉,都像隔靴搔癢。
正因如此,在這系列文章中,我嘗試涉入不同研究模型:前篇文章,我以移民女性身體、城市生活,與別於男性的地理感知經驗,從杜彥穎團隊較為偏重思考的「社區性」、「客家性」面向,推論另一種空間營造、想像及對話可能;本文,我將重點置於臺北「小馬尼拉區」的世界感。其談法,也藉由「洗頭計畫」實踐,再引入更細微的、傳統的、原民的(前殖民時期的生活習慣),或經由全球遷徙/勞動,所浮現的文化生產過程。至於寫作與觀察,兩篇方法與溝通對象之設計,截然不同。然而,它們至少遵循一個共同點:我們無法忽視「東南亞」概念的政治生產與歷史過程,如何使用該詞,應有所醒覺。
在進入下文描繪「中山北路」與「金萬萬大樓」場域特徵前,仍有一事補充:即臺北場「洗頭計畫」的工作方法。過程中,身為「展演規劃者」的 Thinkers’ Studio 須考量如何面對一個「新社群」。原計畫從中壢「火龍果屋」遷移到金萬萬大樓內,不再有深耕地方的團隊能適時協力、照料、甚至預測可能變化的情境。某種程度回應了我 自身於 2019 年的失語情境:當離開「相對安全」的展演空間、離開了印華母親們的客廳、廚房與菜園,進入「新」硬體場域,要怎麼重新銜接新的「社區/群性」?又如 何轉換新的田野經驗與參與方法?幸好,他們邀請菲籍研究生 Al Bernard Velarde Garcia(Al)共同合作,因緣際會下,與「Ganda」髮廊開展破冰與連結之旅。
那麼,金萬萬的場域特性是什麼?對此,作家陳又津(2018/May/29)言簡述及:
⋯⋯是兩棟住家大樓和辦公大樓的連通處,大樓於民國六十多年落成,當時店家以美日、歐洲舶來品為主。一層樓大約有 60 個店面,兩層樓便有上百家。二樓隨處可見招牌寫著菲律賓語(Tagalog),販賣菲律賓小吃、換匯、美髮店、雜貨、 金飾,⋯⋯。
透過陳又津訪談書寫,可約略得知金萬萬大樓空間,曾有過舞廳及舶來品店等特色。該建築蕭條後,上個世紀末,因應菲國社群的宗教和日常消費需求,生產出延續至今的空間使用模態。
金萬萬至聖多福教堂一帶,凝聚消費、交通、信仰中心的便利性(accessibility)。 宗教集會與社交需求是大樓復甦的關鍵。計畫團隊就近消費「東南亞」商品、識懂的 (或感興趣)菲國食物、可溝通的語言基礎,與頻繁「現身」、主動協助店務等表現, 是菲國社群觀察、選擇進而決定參與「洗頭計畫」的親暱/信任程度。
大樓內呈「日」字型。相較大稻埕果品店中庭的洗頭展演經驗(有著「安全、集中」的內向性),在此,無時無刻都要留意店家之間的緊密比鄰。稍加忽略,就有可能造成緊張、衝突或不順。這些複雜感受,實是親暱的展現形式之一。團隊必須時時張開複眼,內視自己的身體「舉止」,是否符合身為大樓主要使用者的菲國社群的行為規範。無論如何,金萬萬擁有自身的「社會秩序」:既符合公寓法規、使用規範,又包含菲國社群在使用空間上的認知與默契(源於前殖民時期的集體傳統),以求某種共同生活的潛在規約、或協商後的節奏。
就此,計畫團隊採取類似於 1970 年代,William H. Whyte(2016)觀察紐約廣場使用者的日常行為,著重記錄使用者於該空間內的相處與感受。我們切身觀察、參與大樓內「非正式習慣」的運作默契:在最小、看不到之處,其實存在著透明的空間界限,乃立基於鄰近店家的相處特性。負責輸水的工作人員,也有自己習慣的勞動路徑。可以說,金萬萬的菲國社群要如何避免因緊密而可能潛藏的衝突,工作場域中的「身體芭蕾」理論和族群傳統結合,會是個值得探究的題材。最重要的是,多次到訪後,對於店與店之間、不可見的領域界限,或是鄰店經營者的個性,我們開始萌生了初步意識。團隊成員的身體,似也開始養成適應該場域的合宜模式:有人提防是否有違 「共識」下的生活習慣(如低聲提醒「不要越線」,但這線是隱形的、與店主由內而 外的監看視線有關),或主動向髮廊周遭的餐車、店家,學習其習慣的語彙,進而協助招客美容、叫賣或販售手錶。
例如,一名年輕店員在我手機輸入:“Pagupit Poki / Ganda”。
“Pagupit poki (來剪帥帥)/ Pagupit ganda(來剪漂漂)”!我以英文發音「怕股屁,波七」,她們聽後大笑,很自然再表演了一次:「O.K.!注意聽!是『把辜北~~~』 波 ki」。我記下:『北』嘴巴要張大、長音,像臺語的「爬」;“ki”略短,以產生吸引人的輕重與節拍。在髮廊雲集、競爭激烈的大樓環境,似乎得將 gupit(剪)一詞,創造出略帶誇張、戲謔的扁音。當我們在外喊到「偷懶」時,直接看到男性就說 poki、 遇到女生即喊 ganda,此舉讓她們在店內愣住,轉而朝外大笑,好似察覺我們正在偷懶,卻又不知自己想要表達什麼的感覺。
當我們發出稚拙的 Tagalog 話,總引來店長和顧客們大笑。即便曾對我們人多而略感不慍、賣著香蕉與手錶的中年婦女,也微笑、善意「矯正」我們的發音。
這便是金萬萬的日常:讓我們的「身體」,轉化為對雙方而言,不造成「多餘或擁擠」的心理感受吧。
我將在下一小節探討「共識而生」。這是擴及空間與社群親暱互動的主要課題。 本節首要回應金萬萬大樓與中山北路的共生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