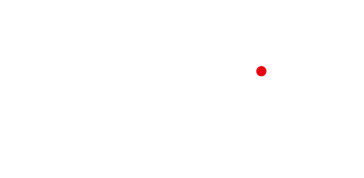文/林正尉
饗宴與洗髮(2);移民女性與身體場景
群體越小,邊界問題就越大,人們就越無法忽視周遭地區的菜餚。–Jack Goody(2017:2)
勞動部 2020 年 6 月底統計,桃園移工人數近達 11 萬 4600 人。(1) 在新住民人口達兩萬有餘、臺灣縣市外籍移工及新住民人口名列前茅的大桃園地區,光是兩座主要車站的異國餐廳與雜貨店,將近 130 餘間,服務境內一萬座工廠的移工及住民的日常需求(沈豪挺、李美賢,2018)。
(1) 勞動部數據:https://statfy.mol.gov.tw/map02.aspx?cid=3&xFunc=32,引用日期:2020 年 8 月 8 日。)
公部門展現的,是講求客觀與科學的統計數字。公開資訊和數據,固然反映著如何符合其日常需求的「族裔地景」,講述特定群體的生活和地理邊界。是物理姿態的;但是,涉及更細微、族裔的、身體的、性別的、身/心理邊界等特徵,待進一步描摹。
一、來臺的移民女性:身體—邊界系譜學
我們首要面對的,是移民女性身體的邊界問題。
1992 年 5 月《就業服務法》通過,與後續的南向政策發展,因應產業外移與缺工、 少子高齡化及兩岸政治局勢等社會趨勢,逐步奠定外籍移民與勞動者的法定制度。移民女性的身體,受警政、社福、衛福與勞動部門等若干資源「協助」,同步意味著隱性監督與刻板印象。在權力機構賦予合法性、轉而強化在大眾媒體上的移民女性,或多或少成了「治安死角」、「忠誠堪慮」、「生育功能」,來自「落後國家」、「健康疑慮」等標籤化客體,出於政治、經濟和社會—生物演化論的殘存遺緒。上述印象, 伴隨「境外面談」、「空間使用」等人權正義議題,於 2010 年前後興起批判及反思。
性別化的身體邊界,涵蓋內外糾纏的綜合因素。看似來自主導、陽剛的階層社會, 帶動人們對移民者的恐懼與期待。這些人為建構的焦慮,蘊藏自內部壓迫的其他因素。
對移民女性身體的期待,訴諸道德論說。其身體受賦予「維持文化邊界」的任務, 背負「民族子宮」使命。邱琡雯(2005:140)敏銳察覺:「移動之後女性移民的族群、 階級、性別、宗教、職業等社會屬性所刻劃出的邊界會產生變化,這種變化帶給女性。移民一定程度的不安」。此是第一類提醒:要如何將性別意識及身分流變的協商過程, 加入移民女性的社會心理學分析,是當務之急。
移民女性的社交、生活空間如何緊縮,是第二層提醒。
全球遷移向來是權力支配下的不平等狀態,並不均質。無法掌握優勢的人,只能被迫遷移,抑或限制其「不動」(Doreen Massey,1993) 。長途遷移的勞動者,不再以男性為主。更多移民女性的趨勢,意味權力不等的現象將更為持續:普遍男性相較後者,擁有更多的遷移自由。棲身於「家」(常指稱為「避風港」),闡述了性別勞務分工的權力配置。難道移民女性相較自由了嗎?
第三種提醒,要問的是:移民女性的多樣性,是否單一了? 這項提問,看似來自前兩者的部分統合,還涉及更多因素與選擇:親族團聚、職業、維繫家族生存,有些人則前往他國尋求獨立/解放等。要如何重新認識移民女性的動態認同,絕非鐵板一塊,關鍵在於察覺移民網絡的支持、社會資源配置,與女性如何敘述自身處境等要素 (參考自邱琡雯,2005:35-52)。
邊界是互動與重新命名的結果。Donna J. Haraway(2010)所謂的女性處境知識, 抑或 Susan Stanford Friedman(2014)的「六種話語」等,(2) 皆說明身分其實是各種充斥歷史意識、因各類關係而結構、定位、交叉、匯集,或身處不同權力處境下的立場樣態,更是不同時/空層次的對話關係。換言之,邊界是不同立場之交叉,及動態交往的空間(ibid., p.23)。
((2) 多重壓迫話語、多重主體立場話語、矛盾主體立場話語、關聯性話語、情境性話語和雜和話語(頁 23-24)。)
二、Ayo Ber-Hidup (一起「做」生活)!
「印尼客家」一詞,充滿複雜外力, 和特定脈絡下的命名政治所建構。
「洗頭餐車計畫」成員,具備兩項主要優勢。第一,桃園藝文陣線的杜彥穎團隊, 已與這群印華移民婦女累積一定的信任基礎。他們學印尼語、前往坤甸(Pontianak;部分這群女性的故鄉)實地走訪,擴充自身與母親們的連結程度;其二,藝術家張剛華出身坤甸北方的山口洋(Singkawang),成長於新竹湖口,在與這群婦女以「母語」 對話時,發揮了關鍵效果。此外,他觸及桃園、新竹一帶的家族/移民網絡,言談間, 共享兩地親友的相似性。言語創造「同鄉感」。這些因素,助增計畫團員與移民母親們,於相處及「工作」上,得以分享更為民主且親近的合作「空間」。
我說的「空間」,不限於具體可見的洗頭與餐車,還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語言切換、 視野開拓、(3) 備料烹煮、菜園澆水等互助行為(gotong royong)。說簡單點,是讓彼此的親暱基礎更為有機、活現,且對上文三種提醒,直指關係更加對等的實踐。
((3) 自 2016-2019 年,我三次前往東印尼蘇拉威西的望加錫,通曉些許印尼話。當母親們相互介紹 「洗頭餐車計畫」時,我的角色,常是「去一個她們從未去過的地方」、「知道當地有什麼」的人。)
透過杜彥穎團隊的「家鄉」親訪經驗,與母親們共構家鄉記憶圖像。他們言談中,不乏坤甸的河流、街區和村莊;加上張剛華的「母語」和地緣經驗,和她們共組可能的地緣網絡/臺灣本地印華人際網絡的地理圖像。這是既直接有效、不拐彎抹角的親密。如邱琡雯(2005:268-272 )所示:具華人血脈的移民女性,認同依戀於父母親和親友,遠高過對原生社會的「國家」認同(後者可能不存在)。透過她們的自我敘事,同樣呼應了邱琡雯的觀察:其對原生社會之所以親近,是在家庭情感與經濟維繫的基礎上;對原生社會的疏遠,則因貧困與排華等壓力。
杜彥穎團隊與張剛華的合作,恰好銜接她們的核心關注:以家為主的巷道與街村;以家人為核心的語言共享;以家鄉為尺度的生活空間藍圖。「洗頭餐車計畫」營造的親密感,甚至化解了人際衝突。(4)
((4) 值得記錄的是:這群母親當中,也曾出現緊張的關係。「洗頭餐車計畫」促使各家分享料理絕活,此舉巧妙改善彼此可能深藏已久的衝突。)
三、菜園的隱喻:族裔性與自然的共生
若你/妳前往「東南亞」商店的香料調理包區,翻至背面,常見幾個桃園地名:平鎮、中壢、觀音、八德與大園。
50 多年前,上述鄉鎮曾存大量陂塘,逐一徵收為工廠與街區用地。這些工廠聚落, 因應石門水庫、高速公路、國際機場、石化工業及聚落遷移等動態力量所拼湊,讓桃園在 80 年代前後,奠定工業及運輸城市的形象基礎。
在那個講求工業崛起的樂觀時代,有人從中部鄉村遷徙至此,經營五金、維修、 外包工程與家具製作;在那個講求都市機能擴張的發展年代,搭上印尼蘇哈托政權晚期的社會動盪,引領一波為數眾多的印華年輕女性遠走她鄉。
其中一位便是「朱媽」。
就都市規劃歷史角度看來,桃園深受專才官僚的理性規劃脈絡所影響:在冷戰及世界經濟體系下,因應美國主導的半邊陲經濟鎖鏈而生,進而帶動本地代工產業與重工業。農業地景和陂塘快速消逝,工廠林立。充滿雄性、陽剛的都市發展特質,盡收於朱媽細心照護的菜園。她那彎腰舀水的體態,面向整齊種植的各類蔬果。菜園小溝, 對比那叢正在快速建起的大樓,光在視覺意象中,產生劇烈對比。
沿著新街溪沿岸步道與綠帶公園,朱媽和丈夫種著與她有關的香料。她的丈夫是當地里長,資源回收告示上,標誌各種「東南亞國家語言」。初訪她家時,我看到這些植栽與帶有善意的語言設施,不覺重省「新街溪」一詞的曼妙:一種帶有母性的新型態街道/公共生活悄然誕生。「與共感」和公共接觸機會的增加,該街廓不因鄰近河畔的低調個性而失去活力。它或多或少關懷了鄰近地區移民/工鄉愁與味蕾。
朱媽繼承家族的烹飪習慣與口味。路旁的香料種植,必然與其記憶圖像有關;早期,丈夫還會一起回坤甸。他的腦海銘刻某些作物的種法。
朱媽家中的私密性,連結街上,進而延伸一處開車十餘分鐘的郊區菜園。
朱媽與里長共植菜園,一方面是兩人身體—實作的地理延伸;二來,如 Patricia Klindienst(2006:6-7)所言,菜園攸關如何認同自身的隱喻。它部分歸屬至朱媽的身體內。這道隱喻,在族群同化的氛圍裡,展現某種抵抗的溫柔姿態:她(們)循沿原家鄉文化的種植傳統,和新家鄉的適應之間,不斷游移,依此形塑新的土地倫理。後者透過植物,連結坤甸與中壢的地景圖像。種什麼,意味著來自何方。
「洗頭餐車計畫」成員,和母親們相處數週歲月:一起做粄、進出菜園、磨香料、 品嚐參巴辣醬(sambal),更重要的,「閒話家常」。過程中,我試與極為內向的朱 媽,以「笨拙」的印尼語對話時,她既嘲笑我的「很多聽不懂」、跟不上、卻意外猜得準,似乎可通。從此我們倆人說話,便是以她的語言為主。她用印尼話告訴我,家 中多說潮州話及客家話。
我們交換了故事。朱媽原先內向與嚴肅,熱切轉向與我們的互動上。對我們「訕笑」,某種程度又成了她對我們的開放。
至此,我想起「世界公民」這個詞。
相對少數的女性,能如作家 Virginia Woolf 般,靠著紙筆勾勒自己身體及家鄉(跳過「國家」概念),直接串起和世界的關聯;更多的女性像朱媽這樣,在一個拒絕給予自己完整公民身分的世界裡奮鬥著( Elkin,2018),從家的廚房、路旁植栽、菜園,再游移回廚房。但是,菜園是個轉折。像「朱媽」這樣的人還有很多。她們與菜園互依共存,既是世界公民的記憶的歸屬,又是心靈所繫和故事聚集之處 ( Klindienst, 2006:241-242)並且在這游移的世界中,建構自己。
四、廚房內的無聲傳說:生活舞臺與饗宴場景
JoséeJohnston及Shyon Baumann(2018:28)曾表示,「食物地景」(foodscape) 夾帶了動態的社會建構,不僅將食物連上地方、人群、意義與物質過程,也包括「以各種方式捕捉或模糊了食物生產與消費的生態起源、經濟關係,以及社會意涵」。食物被視為理所當然,其中的性別向度易受疏忽:
當食物位居男人、市場和生產的領域時,它可以變得很重要,但是日常飲食與維生的領域,卻聯繫上私人的、顯然無足輕重的女性世界。(ibid., p. 73)
事實上,很少有男性願意如法國歷史學者 Luce Girard(2014:203)那樣,跳出來反駁婦女之所以必要準備料理和家務,是種「內在本質」及「應盡義務」。有趣的是, 他承認某些廚房是「啟發各種發明的地方」,好奇願意「花費、奉獻生命中的一部分時間,到不能留下痕跡的事件中去呢」(ibid., pp. 204-206)的互惠行為是如何發生的?
誠如「洗頭餐車計畫」過程中,瀰漫著平凡的日常感,讓我撰寫文章時,遲遲懷疑應以什麼角度切入。我們遇到的人和故事太多了。這系列文章,既非民族誌、也不是逐字稿,而是尋找某種可定錨的筆觸,抓攫些微可留下痕跡的事件。
書寫印華母親們的烹飪—展演實踐,必須從日常當中,提煉出如 Girard 所謂的 「無聲傳說」才具意義。母親們代代相傳的伙食技藝,是以照顧他人身體起居為目的, 在準備料理的重複動作中,回想起菜餚味道及構成(ibid., pp. 206-207),進而與遠鄉產生了多重連結。
她們形象,常以「他人/鄉」而活。
透過「洗頭餐車計畫」,促成更多婦女齊聚朱媽的廚房。她們有著微妙、將原本的國語及客語,轉回家鄉語言的無聲儀式。我們不易察覺。待發現後,她們已開始說著專屬她們的語言,而非丈夫與孩子能識別的話。
母親們協調食材的內部分配,重新配置彼此可配合的時間,對制度化的時/空想像有所衝擊。前言述及:在桃園若干城鎮的食品加工業,日以繼夜,包裝各式料理調味包。罐頭食品與調味包,美其名是方便,至於口味「真不真」,又是另一回事。這些食材的「真」(authenticity),反映的是如何「及格」服務移工每週一日的休閒消遣與味蕾。他/她們必須在一日之內,打理、採買所有生活所需、月初匯款、聚餐會友、家庭通聯、聽經禱告等,有些移工則選擇在工業區附近的陂塘釣魚。他/她們都 一樣,得在規定的時間內返回工廠;印華母親們則不同,有人開設美容院、進修證照考試、開設餐廳,或如朱媽這樣,參與更多的家務勞動。
齊聚一塊烹飪或分送食物,有時是維繫情感,卻又可能招致敵意。有媽媽堅守自己家鄉口味的「原真性」,有的透過上網「進修」新食譜,有些因家中成員口味而調整。應證 Goody 所言,她們或許群體不大,卻可能萌生更多邊界;對家庭內部來說, 即便準備食材及烹飪過程繁瑣,然如 Girard 說的:
準備飯菜可讓人們感覺到一種少有的幸福,即自己創造某樣東西、加工現實的某個碎片、感受到縮小化的造物歡樂這種幸福,同時保證人們受到樸素而精彩的誘惑,重新體會到構成幸福的一切要素。(ibid., p. 211)
這種家中的幸福感營造(或視為日常事務),織構移民女性的移動腹地與意向行為:家中—雜貨店—市場(有時是東南亞商店)—家中的循環。
「洗頭餐車計畫」的饗宴場景,無疑創造這群婦女瑣碎言說的日常延伸。她們有更多的機緣展演—生活的聲音:延展相聚的力道、以自身語言聊聊家鄉、烹飪與家庭感受。更重要的是,廚房—餐車做為可見的移動路徑,繼續延伸她們如何扮演自己角色、 工作組織及其能力的類戲劇舞臺。
飲食習慣深受各種歷史匯聚。對 Girard(ibid., pp. 228-247)所言,「看不見的日常生活」處於無聲系統當中。烹飪時,必要遵守重複且機械般的約束;論及做菜方式, 也得滿足地方的共性,難獨自創造。畢竟,烹飪行為不僅形塑某一群體的日常語彙, 亦表達社會結構中的共同語言,讓彼此訊息便於傳輸、互通。
「洗頭餐車計畫」繼續記錄母親的語彙和食譜,在其身陷日常的無聲系統及種種框架內,這場計畫開創「饗宴」的多元定義。藉由她們的選擇、分配、安排,暫離束縛,順其自身人際網絡延展開來。向來不識彼此的婦女,透過共享相似又有差異的菜餚,產生新的生活連結。可以說:這場饗宴的規畫,使參與者不單停留於各種時間印記(包含生/心理、家庭與社會時間印記),還構築了寬廣、韌性的人際支持網絡。
五、小結
餐桌是種複雜而有效的社會機器,它讓人說話,人們「坐在餐桌旁」後會承認原本不想說出的事⋯⋯充滿樂趣的地方,是個古老的發現,餐桌自有其秘密並保留著事實真相,吃飯永遠不僅是吃飯,它包含的內容比進食更多。(ibid., p. 259 )
行文至此,讀者或許早已發現:本文主角,並非「計畫」團隊。如何書寫,關乎場面調度。書寫也是種角色。在本篇特地安排場景中,它介入了婦女生活與城市空間的若干關係。說淺白點,若無法察覺城市及場域的空間圖像、價值觀及這群婦女的行為日常,我們說不上這個計畫的中介,究竟能扮演何等可定錨、丈量,進而觀察與評析的動能。
我始終認為,這項計畫有助提供某種社會支持系統的另類想像,同樣是另類社區/群營造的新實驗。尤在新冠肺炎襲擊全球健康秩序、挑戰原有生活節奏及普世價值, 迫使人們緩其運行。當前,如何重整自身的世界觀,進而容納新的文化交往形式,是刻不容緩的議題。
「洗頭餐車計畫」行動,不僅關心印華母親的生活情感敘事,疫情時代之下,更突顯「日常」習慣與認知,歷經如何操演、衰退與再生的循環。
「印尼坤甸—她的娘家是我們的冒險」,關心中壢印尼母親們的「客家性」與料理傳承,有其實踐原旨。透過「洗頭餐車計畫」的整合能量,延伸移民女性身體、心理和地理等向度。它以追尋母親的族裔身份與食物傳統的基礎,持續開拓另種組合:合力朝向民主,叩問人際之間的——親暱的多樣性。
參考資料
De Certeau, Michel & Girard, Luce & Mayol, Pierre 著、冷碧瑩譯,2014,《日常生活實踐 2. 居住與烹飪》,南京:南京大學。
Elkin, Lauren 著、許淳涵譯,2018,《漫遊女子:大城小傳,踩踏都會空間的女性身姿》,臺北:網路與書。
Friedman, Susan Stanford 著、陳麗譯,2014,《圖繪:女性主義與文化交往地理學》, 南京:譯林。
Goody, Jack 著,王榮欣、沈南山譯,2017,《烹飪、菜餚與階級:一項比較社會學的研究》,杭州:浙江大學。
Haraway, Donna J. 著、張君玫譯,2010,《猿猴、賽伯格與女人:重新發明自然》, 新北市:群學。
Johnston,Josée&Baumann,Shyon著,曾亞雯、王志弘譯 ,2018,《饕客:美食地景中的民主與區辨》,新北市:群學。
Klindienst, Patricia. 2006. The Earth Knows My Name: Food, Culture, and Sustainability in the Gardens of Ethnic Americans. Boston: Beacon Press.
Massey, Doreen. 1993. “Power-geometry and a 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 in Bird, Jon et al. (ed.). Mapping the Futures: Local Cultures, Global Change, pp.60–70. London: Routledge.
沈豪挺、李美賢,2018,〈桃園後站東南亞街區的變遷脈絡〉,「經緯桃園:2018 桃園學研討會」(未出版)。
邱琡雯,2005,《性別與移動:日本與台灣的亞洲新娘》,臺北:巨流。
Summary
Proofreading|Melody Wagner
This observation turns to immigrant women and their “body-scape”, which concretely focuses on how the art project “measures” urban developmental conditions, women’s daily life, and its cultural mobility.
Th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art project has included understanding the language- switching rituals, co-cooking, gardening, as well as other with mutual behaviors in Indonesia Chinese women’s daily life. Shortly, it makes each the term “intimacy” more organic, open, or alive.
We observed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women’s kitchens, their language, garden and living rooms, etc. A delicate balance between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work and self-identity has been well- organized. Based on it, we began to share our stories and create more intimacy with each other.
“How to write” plays an active role here. The writing – mise-en-scène – involves different kinds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women’s daily life and spatial scales. Also, it is possible to mention that what kind of kinetic and intermediary character within this article and the project, could be read and detected without social bias, and more devoted to their respectful daily behaviors in places, where are so-called “new homeland(s)”.
In my opinion, this project helps to provide an alternative vision of what a kind of social support system will be both now and in the future, as well as a new experiment in community/group relational building. Since now the COVID-19 has been hitting severely, an alternative imagination of cultural geographies of ENCOUNTER has always been an urgent issue, for this project not only concerned with the migration women’s narratives but also highlighted/described the values of “daily life”, the circulation of its decline and rebirth in the global pandemic e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