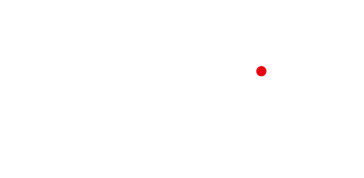文/林正尉
饗宴與洗髮 (1):建構日常表演的詮釋及方法
臺灣近年來於各部門及民間等層面,逐漸累積與東南亞區域交流、認識的豐富能量。這些明顯轉變,亦浮現在表演藝術創作和社區營造工作者身上。
「在臺印、菲社群生活文化交流計畫」(以下簡稱「洗頭餐車計畫」或「洗頭計畫」,兩詞因發生地點而有所不同),是由臺北 Thinkers’ Studio 及桃園藝文陣線共同策劃,並邀請具有印尼華裔血緣的劇場導演張剛華合作而成。
本系列觀察書寫,我將聚焦於「生活」與「表演」辨證上,出於幾個原因與問題意識:首先,相對視「在臺東南亞族裔」為某種集體符號,我更關注的是他/她們是如何成為積極、主動的個體行動者?他/她們在計畫中並非扮演被動的參與者。
第二,我試勾勒這些人的生活及敘事,進一步與兩個主要團隊,及藝術家、參與社群之間的關係。我不僅透過親身觀察,更希望〈饗宴與洗髮〉三篇文章,能形塑一套書寫計畫。它們不僅描繪地方性格與人際關係的複數特徵,更重要的,是指出計畫中的展演意義與價值。換言之,本計畫帶有動態且有機的「展演性格」(performative character):彼此言說、烹飪、洗髮、串門子、巡視菜園等「日常」與「行為」,構成整套「交流計畫」及其核心精神:
「我們」之間,能否更平等、更親密呢?
至此,我或多或少接受澳洲籍越南裔作家黎南(Nam Le)與友人醉語後的啟發與詰問:「族裔文學」充滿對異域料理的描寫,「那些貧乏的語言是作家有意為之,還是詞彙量不足」(2015:8);那怕書寫再無聊,冠上「族裔」一詞,如免死金牌似的,不用怕角色多麼無深度與標籤化了(ibid., p. 9)。
或者,我們也可大方尾隨、承認他的寫作哲學:究竟是挑戰舊有觀念或鞏固它們;還是嘗試創造新觀念?關於寫作或觀察的描述,黎南認為就是創造,創造人們賴以為生的土地。即便黎南說的偉大了,我們仍可從中建構某種可能的書寫思維:至少拒絕過於強調他/她們的族裔背景,而是回歸成具有共同情感的人。
倘若我們還認為這是一場劇場式的展演,這種想法將預期一種閱讀「洗頭餐車計畫」方法的匱乏與困境。我在後續文章將持續深入該計畫的寫作立場:它不從屬某種可被歸類的藝術理論範疇,也將失效於正規的劇場評論方法。像這樣的日常表演觀察, 受限篇幅、受制生活體驗及時間相處時間,使我轉而談論下列三個層次:
- 土地與生活空間的多重創造:它擴及計畫的核心關懷;先有土地和生活,再談創作與參與。前者是構成一切的根基。
- 展演論述:朝往伙伴關係、多方建構、圖像中介的,和自我組織/培力的共創性格。
- 生活感與親暱性如何維持?這是本計畫涉及「生活」與「表演」的模糊分際。
一、「洗頭/展演」若干系譜
「洗頭/展演」並非新鮮事。早在人類學領域的生命儀式研究、傅柯式的身體規訓與權力論述等皆有涉及;近到時尚設計、護髮美容、身體政治與快感服務 (Wolkowitz, 2002:張晉芬、陳美華,2019),和個人衛生管理等領域有關聯。
Robin Bryer(2005)《頭髮的歷史》檢視繪畫中的毛髮,連結時尚與歷史,提出有趣的髮式史觀;藝術表現上,時尚理髮師 Rudi Lewis 和攝影家 Julia Hetta 合作《頭髮儀式》(The Ceremony of Hair)展演計畫,發表於 Beauty Papers,針對毛髮的生命禮儀、文化遺產及信仰差異作出討論。1
此外,美籍拉丁裔藝術家 Celia Herrera Rodríguez,曾在其互動性劇場作品《神聖洗髮典禮》(“Sacred Hair Washing Ceremony”),以水盆、梳子、洗髮液、毛巾與鼠尾草(sage)打造「祭壇」。她先要求「觀眾」不得攜帶酒精飲料入場,再燃燒鼠尾草煙以淨化「祭壇」場地。藝術家徵求志願者,參與洗頭計畫,進一步聊到墨西哥的原生家庭、引導「觀眾」討論家族祖母們的護髮食譜。在鼠尾草薰氣與洗髮草藥 祕方沉潤下,彼此以「頭髮」帶動「家族敘事」,成為共通話題。這些因素讓「空間氛圍變得既崇敬、輕鬆和親密」(Ramírez & Casiano[ed.],2011:129)。
Celia Herrera Rodríguez 的「洗髮典禮」,不僅中介劇場與家庭記憶、親密與神聖之間,更尤甚之,「藝術家」如薩滿(shame)般在場,是此儀式性作品的組成關鍵;然而,桃園中壢版「洗頭餐車計畫」,更像是一場有機組合。其「綜合」不僅 源自張剛華從個人洗頭故事,到跨國(泰國、菲律賓等)洗頭計畫的延伸,也包含杜彥穎等人發起「印尼坤甸—她的娘家是我們的冒險」的社群經營基礎;2 這項合作同樣意味了根基於臺北大稻埕的思劇團,和中壢的桃園藝文陣線,模糊原本的專業疆界,展開跨地協作的可能。即便不同計畫來自不同脈絡和支持,這般整合與共創的實踐, 思考了不同地域的團隊,暫時告別可能存在的屬地主義(即僅關注自身所屬地域上的特定行動和議題),主動深化或開拓某一議題的契機。
二、Allan Kaprow:日常生活與展演的模糊分際
應如何同時貼近不同社群的日常生活,且抓住一個不因真實情節轉換而散渙的觀察視角?我認為,建構一種新型態展演論述的認識論,是迫切需要的。這種閱讀方法, 既具彈力、黏著、螺旋捲入可能觸及的日常生活場景、印尼華人媽媽的居家廚房、里長的菜園,和臺北金萬萬大樓中的菲律賓沙龍髮廊「Ganda」⋯⋯等。
我們面對的,是一連串場景變化與偶發。建立一個短暫的日常展演理論與觀察方法,目的也在於「有效捕捉場景與動態的多樣性」罷了。說穿了,「洗頭餐車計畫」 是個不同於一場制式的劇場環境中的展演,任何場景、居民、言說與食材等,都是介於其中的「展演—行動者」(actants-within)。
偶發藝術家 Allan Kaprow 的思想資產,對這項任務使命而言,深含歷史貢獻。他提醒「所有像藝術的藝術根源,都可以被分割及特殊化;相對的,所有像生活的藝術卻是相連而廣角的認知」(Kaprow, 1996: 285)。前者造就了可分離、有限制的「作品」;在他眼中,像生活的藝術並沒有明顯輪廓來傳遞特定訊息。唯有不斷對話、改變。面對或創造這種貼近日常的藝術,其角色在於提供一種(重新)感覺事物的方法, 而非數量上的功能。說得更直白點:僅僅將自身關注,放在「生產實際的作品數量與 特定活動」的藝術家(ibid., p. 250),並非 Kaprow 關心的對象。
「日常」的重新演繹,勢必引起新目光。Kaprow 認為,創造「再經驗」日常的方法與感覺,在「自然」中意識其中的「不自然」。過程裡,「表演者」模糊了身分, 他/她可能成為「之間」的觀賞者,處處留心正在進行中的各項活動。此時,策動非戲劇性表演的「藝術家」,讓選擇變得重要:
創作某種形式的表演是其中之一,在藝術中創造非藝術則是另外一類。非藝術的藝術,運用於表演上,指創造一種與被稱為藝術表演不相同的表現。藝術表演是屬於被稱為戲劇的那一類。一位選擇從事非藝術表現的藝術家,他僅要了解什麼是戲劇性的表現,並且刻意地避免它就行了,至少一開始是這樣。(ibid., p. 247)
這種貼近日常的「藝術家」,可能對藝術世界要求的資格漠不關心。有趣的是, 非藝術展現,提供某種類藝術的感受經驗與活動,給予有藝術想法的人,進一步興起其他理由來欣賞之,不必再以藝術品的形式來評斷(ibid., p. 249)。他/她,可能再使日常生活細節變得重複,觀察其「創造」或經營的連續表演中,所帶有尋常與不尋常之處;他/她不僅是個「藝術家」,同樣兼任調查、研究、實習、留意、感覺者與創造者等多重身分,有意識為藝術世界帶來的分離感,重新鑲嵌、縫補日常生活及美學化世界的孔隙。
三、Christoph Wulf:圖像式展演
Kaprow 論點或許有些抽象了。此時我們可適時摻入教育人類學者 Christoph Wulf (2018)及其「文化表演」理念。這將讓偏重日常實踐的「洗頭餐車計畫」,多些具體參照。
Wulf 論及「文化表演」時,首先宣稱了圖像的貢獻與能量:首先是各類圖像之間的想像力,和想像世界在「人」身上扮演何種角色?於此,他區分四種圖像:感官經驗圖像(各種感官經驗)、內在圖像(記憶、願景、「不在場性」)、審美作品圖像和象徵符號。後兩者是多數藝術作品追求的。
最主要的「洗頭餐車計畫」參與者,是來自印尼坤甸、棉蘭等地的華人婦女,以及金萬萬大樓內的菲國社群等。計畫團隊透過田野調查,赴里長家菜園灌溉、進入朱媽媽等人的廚房做粄、共享剝蒜、磨椒的氣味;而藝術家張剛華協助菲律賓沙龍老闆娘,替客人洗頭。
從「劇場製作」這種講求效率、分工、可控制的觀點看來,這項計畫的過程相當 繁瑣。在此,「製作」、「劇場」等詞,被計畫與團隊淡化其可能帶有的權威意義; 另一方面看來,重複與繁瑣,正是其意義所在:母親們協力做菜的互通口語,如何變得與家人不同;刀法、園圃的蔬菜用途等微妙差異,訴說著不同家庭有其認識方式與習慣;客人所需的水溫與力道如何臻於適中,則需要不斷嘗試、施做,內化成「默會知識」。對 Wulf 來說,這些實踐活動的發生,實與圖像模仿與生產有關:
幫助自我與他人、自我與周遭世界關係的處理與表達。想像是圖像的棲身地,是模仿性圖像的所矢之的;想像又是圖像的流動性模仿,是表演互動的開始。 (ibid., p. 3)
藉藝術能啟動的創造性,編織「無可預期」的潛能,使上述內化的日常實踐活動, 擴充其想像力。它帶來社會關係的動態展演,提供類藝術的感知向度。從原先、傳統以家中婦女為主的廚房,促成共同參與的遊戲氛圍。
Wulf 認為遊戲過程中的角色與身體具有雙重特性。這些移民婦女在原鄉,所習的廚藝,根源自其母親、仿自原生家庭;離開原鄉後,親友與街坊更為重要。杜彥穎等 人餐車實踐,成了中壢區域的印尼華人母親們情感連結的特殊中介裝置。
此外,田調累積的會面與對話,醞釀出的遊戲感與表演感,會因不同參與人、地 點、體態語言、時間流程不同,產生新的身體感知,「基於想像力,知覺和情感又得以『塑形』」(ibid., p. 17)。
四、小結:朝向新的觀察/書寫方法
我將於後續文章描繪「土地與生活空間的多重創造」、「展演促成生活感與親暱感的再黏著」、「展演共創」三面向的動態關係。
值得再次覆誦:先有土地和生活,兩者建構第一層的親暱性。而後,原為「劇場導演」身分的張剛華,必須消弭、擴大其對文本/演出製作的「導演」身分,轉向對計畫與過程的「導引」(directing),後者更充滿變動與冒險的趣味。
倘若我們同意 Suzanne Lacy(2004)探討過的:新類型公共藝術重視不同社群協如何協作的過程,本身的藝術性具有公共利益導向的特質。那麼,「洗頭餐車計畫」 扮演著是一種關注「社群營造」(community-building)的新類型藝術展演方法嗎?無論是或不是、介於其中、成熟與否、或根本不在乎⋯⋯,這項書寫計畫,就有必要叩問、檢視其黏著的社群意義、價值與空缺;同時,〈饗宴與洗髮〉系列文章,也須適時表明觀察者的在場意義。將它們視為「導引」吧:「洗頭」的「展演」的藝術意義, 是如何從內部轉化及塑形的?
透過張剛華的洗頭構想,婦女在戶外談論自己想親自洗髮的家人(已逝父母), 並從旁觀的觀眾群中,「挖掘」符合其若干特徵的參與者,具有記憶性和圖像性。由婦女們幫選定的觀眾洗頭,藝術家退身其後,致力延伸其敘事氛圍。運用指尖、水溫、 泡沫傳遞思念,重新營造一種既公開又私密的新場域經驗。
「是否為表演」?這是合作團隊時常探討的:「究竟如何談論這項計畫」?就我觀察,本計畫具有深度的展演特質,卻需要仰賴不同社群的生活為認知前提,以及一 種等待建構的認識論。
張剛華與杜彥穎等人,來自不同實踐、動因與脈絡。然而,書寫,導引「洗頭餐車計畫」的異質元素得以重新匯流的可能,共創出:既能與 Kaprow 的「日常實踐」對話,又擴充居民、婦女和學生們的合作空間,進而掀開原鄉記憶圖像、新的家庭圖像及可意識到、改變中的鄰里關係等行動面向。
若承認書寫有其必要存在的價值,「書寫」,於本計畫的脈絡中,遂開始享有其角色上的展演意義。
參考資料
Bryer, Robin 著,歐陽昱譯,2005,《頭髮的歷史》,臺北:臺灣商務。
Kaprow, Allan 著、Kelly, Jeff 編,徐梓寧譯,1996,《藝術與生活的模糊分際》,臺北:遠流。
Nam Le 著,小水譯,2015,《船》,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Wolkowitz, Carol. 2002.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body Work.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16(3), pp. 497–510.
Wulf, Christoph 著,陳紅燕譯,2018,《人的圖像:想像、表演與文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張晉芬、陳美華(編),2019,《工作的身體性:服務與文化產業的性別與勞動展演》,新北市:巨流。
Summary
Proofreading|Melody Wagner
In “Cultural Life Exchanging Project of Indonesian and Filipino Communities in Taiwan” Project, I will discuss the concept between “life” and “performance”, which are not told to be divided within the action. The plan owes a dynamic and organic “performative character”, involving in “daily” and “behavior” such as talking to each other, being aside with neighborhood, cooking, hair washing, home-visiting and patrolling the gardens, which forms the core theme of it.
We will meet that the scarcity and dilemma of a theoretical method toward how we understand the Project, since it would neither fall into the categorized art theory nor fall into the formal methods of theater criticism.
According to Allan Kaprowian legacies and viewpoints from anthropologist Christoph Wulf, that we need to build up a connection and viewpoint toward daily-life and performance.
To sum up,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stablish a temporary theory and observation method for daily-life-performance in order to “capture the diversity of scenes and dynamics effectively “. In this project, it is a unique performance genre that differed from an institutional art scene. Here, the residents, local community, casual conversation, and food, are fully expected to be “actants-with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