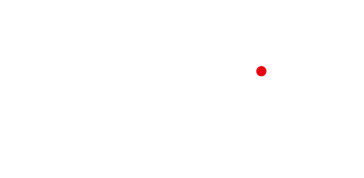文/周寬柔
在新加坡的每天都需要很長的放空和睡眠時間。
各式磁磚招牌、廟宇和熟食中心、各種族人的樣貌和特徵疊加,待在這個城市什麼都不用做,光是眼睛睜著都會被繁雜的圖像和符號式資訊敲擊腦門;
光是打開耳朵都可以同時聽到數種語言,每種語言都因為混雜的語境而加乘各種腔調和用法。當地人行雲流水的語言切換,如同一看到我就展現輾轉(liàn-tńg)台語的印度奶奶,相較之下,第三天我連母語中文都開始結巴;
光是呼吸,氣味都形成各種曲折的場景。正因小印度區各種香料、汗臭與古龍水夾擊而暈眩時,突然聞到熟悉的、如同救贖一般的紅包香。或是一進到7-11,所有味道突然被抽空,如同生命的多樣性被塞進一個個塑膠袋,被編碼變成商品;
光是食物,或是說用餐空間與用餐方式。我已經放棄分辨這是哪種文化下的產物,沒意義。
最奇妙的是在這樣極度「混」的樣態之下卻又是高度秩序化的,大至城市區域分配(ex.在熟食中心你東西吃完沒拿去回收區要罰錢哦有攝影機在看你)、居住空間(ex.公寓一層裡面規定要有三種人種的家庭,是用分配的)、交通(ex.悠遊卡沒有給你用到負額這回事),小至活動參與前一而再再而三的信件提醒與詳細的announce,都像在複合式的城市身體裡進行超精細的數據檢查。
當我在感受這幾天身體的狀態時,驚覺並不是從a環境到b環境那麼簡單。從臺灣到新加坡的身體像是從恆定的狀態到”分裂作為一種常態”,只有每每回到安靜的飯店房間,才有辦法一塊一塊拾起意識的碎片,還有文字。
前天在新加坡最高學府(NUS)參加傳統馬來舞論壇,主講者幾乎都是華人,參與者幾乎都是馬來人(女性多數可辨識為穆斯林)。我只有參與第二天,討論的內容聚焦在社區藝術、舞蹈治療和長青舞蹈。後段有一個設計給長者的示範工作坊,由兩個帶領者一起帶領著論壇中幾乎都是青年的參與者。
回想起來那是我參與過最富有政治意味且多重扮演的舞蹈工作坊。
兩位帶領者排好先後順序,用自己的語境和方法帶領數個馬來傳統舞的基本動作。
第一位帶領者是我這次主要交流的藝術家Hasyimah Harith。作為馬來穆斯林女性、視覺藝術背景的傳統舞創作者,他用想像與即興的方式在理解和教學馬來傳統舞。傳統舞對他來說並非舞蹈技巧,而是一種與自身、與家庭和社區產生流動關係的身體。而在他的動作引導裡,更多的是去想像傳統馬來部落的光景,部落裡的人如何產出動作、如何為動作命名。參與者不只是複製動作,而是透過動讓身體進到意象空間當中。
第二位帶領者是以社區劇場為專業的梁培琳教授。他以精準的數字和身體骨骼類的專有名詞很細節的介紹動作如何被構成,透過肌肉如何用力,可以達到如何的運動效果與身體益處。作為舞蹈系畢業的我馬上連結到學校所教的芭蕾、現代舞派別等西方舞蹈訓練方法,更有趣的是在引導中還加入了太極引導的運氣方法。
這兩位帶領者的身份與方法各有其政治體現,而作為參與者,在兩者被擺放在一起的「多元」交錯之下,可清晰地感受到外部(場域中)與內部(作為參與者的學習錯亂)的分裂與衝突,同時還要去設想(扮演)某種長者的disable狀態以便工作坊順利進行。
從這個的身體經驗去理解第一段提到的「混」種的城市身體,不只是感受,我覺察到的更多是政府如何制定政策與我作為一個外來人的自身反應狀態。
有一次走進捷運,車門一打開清一色印度男性。走進車廂我感覺到身體下意識的縮緊、呼吸變薄,直覺的想要不要走到別的車廂。察覺此自身反應後,馬上批判自己這樣的變化到底是作為一個女性身體經驗者,還是作為一個臺灣人(還是外省第三代)?我回想到在臺北捷運有時會碰到一大群移工或是新住民,在相視的0.01秒我們一定在當中交換了什麼,我卻永遠無法知道他到底從我這裡收到什麼訊息。
對於反應差異他者的身體直覺無法說謊,只能意識並從裡面更知道自己是怎麼樣的人。
新加坡符合我對於「當代」極大值的想像,這裡面除了「多元」、文明等意象,也包含了某種投機性,比如印度廟和觀音堂比鄰而居,華人拿香拜完觀音反正香都點了還是會拿去拜一下梵天。(那間印度廟是唯一我看過門口有香爐的)
基於在da:ns lab對於identity的梳理,上面的文字提到了各種identity的名詞與定義,有些出於本人,有些出於我的(可能暴力的)臆測。Identity是公眾性的(個體/自身亦可作為一種公眾),如同我寫下呈現給公眾的文字中,所有定義的用意在於提問與實驗,所以若任何誤用/誤解,讓我知道對我來說是一件很棒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