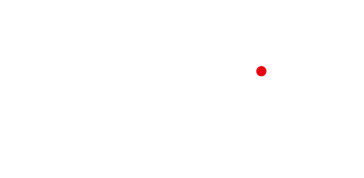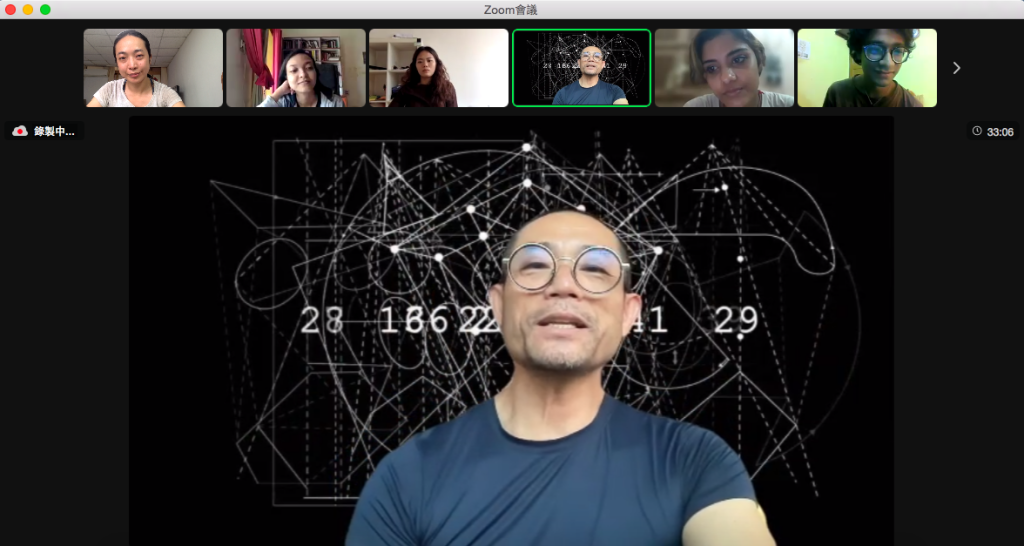觀察書寫員/李芷蔚 Lee Tsz Wai Vivien
《女殊運動》起源於2021年4月由思劇團舉辦的「東南亞性別網絡計畫:雲端駐村」,兩位共同創作藝術家陳詣芩及周寬柔雖身處台灣,但借助線上駐村方式與新加坡、泰國及菲律賓等東南亞藝術家進行交流,從中衍生《女殊運動》的台灣原型。帶著這個原型,《女殊運動》緊接著在7月至9月參與東南亞地區國際策展人組織Karakoa Incorporated Association舉辦的Creators’ Cradle Circuit 2021: Transnational Mobile Festival Loei & Tokyo(簡稱3Cs計畫),再次以線上方式與泰國及日本藝術家進行合作,在泰國Low Fat Art Fes及日本東京BUoY Festival發展《女殊運動》的泰國版與日本版之田調、影像及階段演出。在半年時間內,《女殊運動》從純粹的台灣本地跨代女性身體和性別思維踏尋,發展成具更廣國際文化累積的東南亞跨國女性社會思考計畫,其可貴之處也許不在計劃規模之大小,而是隱藏於國際交流過程,對作品及藝術家本身所帶來的開放性與公共性塑造。
《女殊運動》內容著眼於跨世代女性的性別對話。藝術家以田野訪談方式整理和探討不同年齡層及國籍之受訪女性在各自面對社會浪潮時的思考與應對,形成不同社會文化背後的「女書 (1) 」。在計畫開展之前,我們卻未曾想像《女殊運動》在面對田野參與者及國際協作藝術家時,竟可引來此等多向資訊流動與集體自我觀照能量。當初藝術家帶著源自台灣的文化觀察與想像進入另一個國度,固然理所當然地外化著台灣文化下的女性思考,期望交互兩地對女性生命經驗及標籤的思考。然而因著這次國際交流旅程,讓我們有機會從他國女性的角度,內化她們基於《女殊運動》提出更開放性的詮釋、文化反觀和自我提問,借用她們的手,共同反覆雙向地揉捏著計畫沒有形狀的形狀。
作為計劃製作人,筆者在計劃期間常說《女殊運動》是一具魔力的計畫,它具有相當大的開放性,沒有預設的形狀,沒有要為女性的思考賦予觀點,甚至沒有為「女性」二字下定義。它就是單純真實的與計畫中每位女性來回對話,妳的生活是怎樣的?妳成為妳想成為的樣子了嗎?當下回覆的「妳」真的是妳嗎?計畫容讓每個人去代入、聯想、好奇,溫柔有力地集體進行一場雙向的思考運動,而這種反觀性完全超脫地域文化的限制,反而會因為文化背景差異對比,讓雙方都有機會跳躍於似又不似的國際文化間,開放地回看那些我們過去不假思索的社會定型與性別標籤投射,埋下各自持續找尋自身文化背景獨一無二的女性定義的動能。在筆者的角度,《女殊運動》一方面體現藝術給予大眾跳脫現實的自我觀照和治愈能量,同時也見證藝術家在國際交流計畫中的創作權力下放所帶來的開放性和公共性。
隨著藝術展演愈發重視體驗和參與,不少藝術家都嘗試在創作過程和呈現時進行不同程度的權力下放。在《女殊運動》中,國際交流情境更是推動兩名藝術家下放更多的創作權力。從台灣的創作原型開始,詣芩及寬柔就故意在創作過程及呈現設計上往後退,致力在計畫中糊化所謂藝術家、協作藝術家和田調對象之間的身份和權力限制,為計畫的開放性和公共性發展提供空間。比如在呈現時,詣芩及寬柔刻意退居幕後,請協作藝術家主導活動,請她們用自己的理解,向公眾說明她們從自身及田調對象身上了解到的《女殊運動》精神,並試著以她們生命中的性別經歷或觀察,激發更多人的思考擾動。這樣的設計一開始是為了讓協作藝術家及田調對象的思考不受原藝術家先入為主的觀點所干涉,保持這場運動的有機性。然而到了後來,當計畫走向更多不同城市,卻漸漸促成另一種計畫未預期,更平等、更有廣泛度的思考流動。協作藝術家和田調對象慢慢從被動等待說明的狀態,推進到會按照藝術家提供的線索,主動反思、連結自己和身邊女性經驗,最終產生與藝術家截然不同的理解和觀察,把思考延續到計畫之外。這些意料之外的回應和擾動,一方面不斷讓藝術家與參與者的角色平等化,雙方都能以此發現自身與他人的異同,從中釐清自己身處文化中的性別思維限制,雙向地重新形塑各人更具思辯性的觀點。另一方面也讓《女殊運動》在短短半年間,成為超出我們想像的一場社會行動,在藝術價值上產生無法預估的隨機性發展。可以說當《女殊運動》完成這場國際旅行,它已經不再只是陳詣芩及周寬柔的個人創作,而是成為所有參與過的人們的公共集體創作,未來每個人都可以帶著當中的思考持續屬於他的《女殊運動》。
然而,回到藝術家本身,在個人創作和國際交流中保持開放及隨機性,又要能確保不流失計畫初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姑勿論《女殊運動》本身具相當開放性,當一個創作計劃需要在短時間遊走於三個國際平台,面對不同展演目標定義、製作流程習慣、文化價值及語言轉換、乃至三地藝術家之間的創作方式和節奏磨合等,絕對會消耗藝術家大量精力。加之國際疫情情形不停變動,線上「點兵」和每日一變的展演條件,更是不斷考驗和練習藝術家的耐力、定力與靈活性,一不小心就會讓藝術家在權力下放的同時,喪失對計畫的控制。
這個過程,作為製作人,卻看到兩位年青藝術家從4月第一次參與國際交流的羞澀,高速成長為懂得在國際製作變動中,如何適當平衡放手及堅守計畫藝術設定,身經百戰的藝術家。這種高速成長和經驗積累,除了依賴藝術家的個人素養和成長潛力,同時也是作為計畫搖籃的Thinkers’Studio思劇團給予的培力加持。作為民間獨立藝文平台,思劇團借著與藝術家建立深厚的信任關係及其過去豐富的國際交流經驗與視野,在過程中一路陪伴、引導和支持著藝術家的創作及思考,彷彿娘家的溫暖給予了藝術家在國際平台間逐步前進的底氣。同時作為民間獨立藝文平台的彈性和自由也讓藝術家可以得到更為客製性的資源和經驗跳板。藝術家雖不是從在此間得到衣食不愁的資源供給,但卻可以肯定地與平台機構間得到更具公共性的資源共享、共學、創作思維策略整理及情感陪伴。在更長遠的藝術家自我成長和藝術公共化願景來看,藝術家若能從交流計畫中同時學會此等思維,將是社會更宏觀的珍貴收獲。
筆者一直相信,藝術是社會的公共觀察手段,藝術創作則是人與人間持續流動的溝通過程,國際交流更是把單一的社會溝通上升到更複雜的情境當中。然而萬變不離其宗,我們都在過程中不斷學習如何表達與產出,同時開放地內化他人的思考,最後形塑出屬於我們獨一無二的觀點與公共價值。
————
(1).「女書」,又名江永女書,是一種專門由女性使用的文字,起源於中國湖南省南部永州的江永縣。女書的存在,主要是由於過去思想女性不可讀書識字,即所謂「男書」,所以女性發明女書,以作為姊妹妯娌之間的秘密通訊方式。